闪电手张占魁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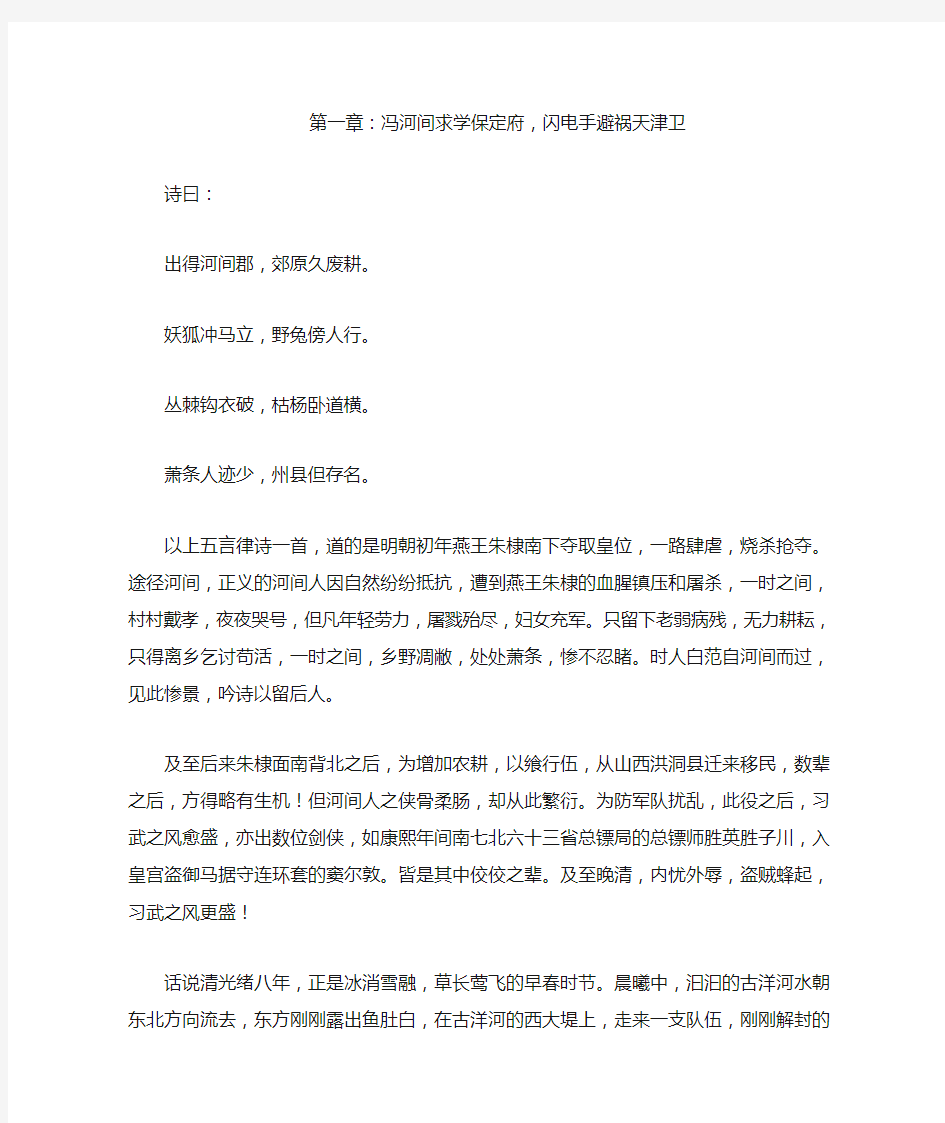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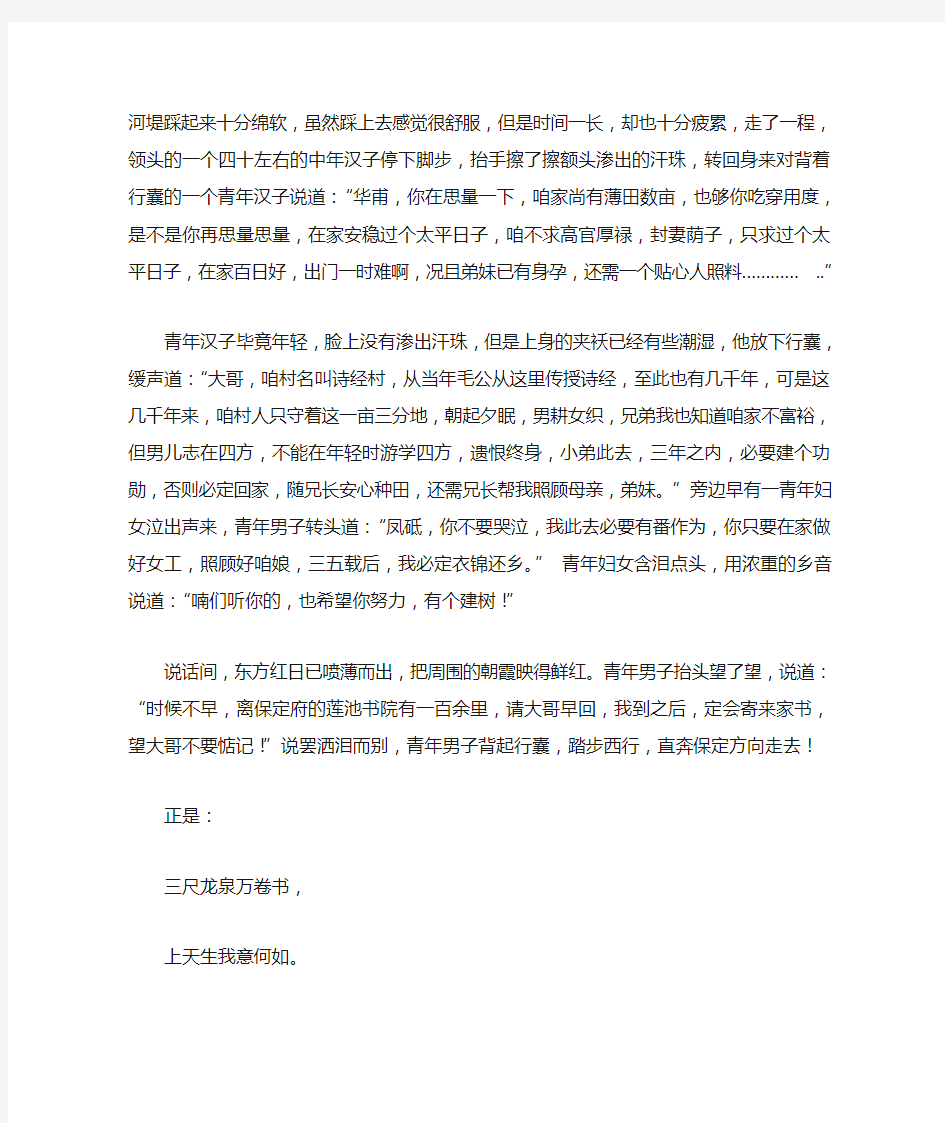
第一章:冯河间求学保定府,闪电手避祸天津卫
诗曰:
出得河间郡,郊原久废耕。
妖狐冲马立,野兔傍人行。
丛棘钩衣破,枯杨卧道横。
萧条人迹少,州县但存名。
以上五言律诗一首,道的是明朝初年燕王朱棣南下夺取皇位,一路肆虐,烧杀抢夺。途径河间,正义的河间人因自然纷纷抵抗,遭到燕王朱棣的血腥镇压和屠杀,一时之间,村村戴孝,夜夜哭号,但凡年轻劳力,屠戮殆尽,妇女充军。只留下老弱病残,无力耕耘,只得离乡乞讨苟活,一时之间,乡野凋敝,处处萧条,惨不忍睹。时人白范自河间而过,见此惨景,吟诗以留后人。
及至后来朱棣面南背北之后,为增加农耕,以飨行伍,从山西洪洞县迁来移民,数辈之后,方得略有生机!但河间人之侠骨柔肠,却从此繁衍。为防军队扰乱,此役之后,习武之风愈盛,亦出数位剑侠,如康熙年间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的总镖师胜英胜子川,入皇宫盗御马据守连环套的窦尔敦。皆是其中佼佼之辈。及至晚清,内忧外辱,盗贼蜂起,习武之风更盛!
话说清光绪八年,正是冰消雪融,草长莺飞的早春时节。晨曦中,汩汩的古洋河水朝东北方向流去,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在古洋河的西大堤上,走来一支队伍,刚刚解封的河堤踩起来十分绵软,虽然踩上去感觉很舒服,但是时间一长,却也十分疲累,走了一程,领头的一个四十左右的中年汉子停下脚步,抬手擦了擦额头渗出的汗珠,转回身来对背着行囊的一个青年汉子说道:“华甫,你在思量一下,咱家尚有薄田数亩,也够你吃穿用度,是不是你再思量思量,在家安稳过个太平日子,咱不求高官厚禄,封妻荫子,只求过个太平日子,在家百日好,出门一时难啊,况且弟妹已有身孕,还需一个贴心人照料…………..”
青年汉子毕竟年轻,脸上没有渗出汗珠,但是上身的夹袄已经有些潮湿,他放下行囊,缓声道:“大哥,咱村名叫诗经村,从当年毛公从这里传授诗经,至此也有几千年,可是这几千年来,咱村人只守着这一亩三分地,朝起夕眠,男耕女织,兄弟我也知道咱家不富裕,但男儿志在四方,不能在年轻时游学四方,遗恨终身,小弟此去,三年之内,必要建个功勋,否则必定回家,随兄长安心种田,
还需兄长帮我照顾母亲,弟妹。”旁边早有一青年妇女泣出声来,青年男子转头道:“凤砥,你不要哭泣,我此去必要有番作为,你只要在家做好女工,照顾好咱娘,三五载后,我必定衣锦还乡。”青年妇女含泪点头,用浓重的乡音说道:“喃们听你的,也希望你努力,有个建树!”
说话间,东方红日已喷薄而出,把周围的朝霞映得鲜红。青年男子抬头望了望,说道:“时候不早,离保定府的莲池书院有一百余里,请大哥早回,我到之后,定会寄来家书,望大哥不要惦记!”说罢洒泪而别,青年男子背起行囊,踏步西行,直奔保定方向走去!
正是:
三尺龙泉万卷书,
上天生我意何如。
不能治国安天下,
妄为男儿大丈夫!
青年男子后来弃笔从戎,驰骋疆场,成为赫赫有名的中华民国第三任总统——北洋三杰中的冯国璋!
不提冯河间一路之上的饥餐渴饮,晓行夜宿。单说日光初起,送行队伍也自散去。闲人不表,且说送行队伍中有一个十七八岁的青衣少年,漆黑的大辫盘在头上,白净面皮上生的一双浓眉大眼,炯炯有神。一身灰布衣衫,虽然破旧,倒也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举手投足,都显得干净利落!书中暗言:此人正是冯国璋“冯家大院”的护院保镖,因其身手敏捷,武功甚好,人送绰号“闪电手”张占魁。张占魁自十几岁便跟随其父,来冯家大院做护院镖师。等到他十六岁成人后,张占魁的父亲便将他留在冯家大院,自已因年老回家种田。张占魁在冯家大院这五六年间,和冯国璋结成莫逆之交,冯国璋教他识字读书,他教冯国璋一些棍棒拳脚,主仆二人形影不离,食则同桌,卧则同塌。直到冯国璋娶妻,二人才有了正式的主仆之礼,但感情却也愈发深厚。
且说“闪电手”张占魁送走冯国璋之后,心中烦闷,郁郁不乐。此时天光早已大亮,也不需巡逻护院,张占魁便信步来到诗经村旁的二十里铺村。这二十里铺村虽说只是一个村庄,但却是南北通衢的要道,南方诸省北上北京,北京南下诸省均需路过此地,因此,这里一时之间十分繁华,南来北往,人流不绝。正街
是一条南北大街,足有五六百米长。商贾云集,店铺林立。游走江湖卖大力丸的、打把势卖艺的、说唱口技曲艺的、占卜算卦的、乃至老鸨暗娼各色人等多汇于此。
张占魁信步走进一家一家饭铺,找了靠窗的一个座位,随便点了两个小菜,想起冯国璋求学此去一走,不知何日才能重聚,心中甚是不爽。为解烦忧,点了半斤白干老酒,自斟自饮,消磨时光。不觉间已是日上三杆,街上行人愈来愈多,有买有卖,有公差,有私事,有凡夫,有走卒,往来穿梭不断,买卖吆喝,也是此起彼伏。
此时是农历二月天气,农谚曰:“二八月,真难过、早晨冷,晌午热。”虽然早晨河里时不时还会出现一层薄冰,但是中午夹袄已不能穿在身上,闪电手心中烦闷,又喝了半斤白干,额头上竟也冒起热气来。于是脱了夹袄,放在一边,半倚半坐,昏昏沉沉。忽然外边一阵嘈杂,搅得闪电手十分闹心。张占魁不禁抬头向窗外望去,见街上人群中一老一少正在卖唱。只见那老者头发全白,稀疏的几根头发匝在脑后,如同炊帚一般,满脸皱纹楼满尘土,双目无神,好像欠了几顿饭一般。灰布袍补满补丁,腰上拴着一个花鼓。身边站着一个姑娘,十六七岁含苞待放的年龄,一身碎花衣衫,也是打满补丁,怀中抱着一个旧木琵琶。
有诗为证:
一翁一女站街前,风尘仆仆着旧衫。
花甲老翁弯腰背,二八少女美容颜。
凤阳离家逃荒客,河间歇脚乞讨钱。
自古离乡人皆贱,落魄行迹使人怜。
只听老者清了清沙哑的嗓音,道:“我父女自安徽凤阳而来,因我家中遭了大水,瘟疫盛行,我老伴病死家中。家中本有二亩薄田,但因遭天祸,颗粒未收,故此我父女一路行乞到此,想天子脚边,洪福遮盖,必能有口饭吃。今小女幼时学过花鼓词,老汉也粗通韵律,不能受诸位贵人白白施舍,我父女二人献上几首小曲,也请各位达官贵人施舍一二!”
说罢,向在场诸人作了一圈揖,捡起二胡,开始弹奏演唱。卖唱父女先演唱了一段凤阳花鼓词,唱道:
“说凤阳,道凤阳,
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骡马,
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
手拿花鼓走四方……..”
姑娘正是二八妙龄,不但模样长得俊俏,嗓音也如同流莺婉转,如诉如泣,分外动人。一曲唱罢,全场景鸦雀无声,听着唱出的调子,再看看眼前的光景,心肠软的都禁不住落下泪来。
老汉生怕冷了场,急忙提高嗓音,对周围人群大声说道:“下面我们爷俩再唱几首本地小调,请大伙不要见笑!”说罢向姑娘看了一样,姑娘会意,急忙擦掉腮边粉泪,继续演唱。这一次唱的是诗经里的《蒹葭》一曲,只听姑娘唱道:“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歌声婉转动人,即使上个世纪当红歌星邓女士也未见得有此嗓音。
正当唱道“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时,场外有人起哄:“所谓伊人是不是你呀?在水一方是不是在等我呀?哈哈哈..........”常言道:十里之乡,必有仁义,十里之乡,也必有歹徒!古往今来,皆是一理。对于常年行走江湖的这对父女来说,根本不以为意。父女二人未加理会,继续弹唱,一曲终了,老汉拿起破簸箩,开始向围观的人群求施舍,但走到两个公差模样的大汉面前时,老者摇摇簸箩,道:“二位官差大人,看我父女可怜份上,乞求施舍点米饭钱………….”话音未落,一名凶巴巴的官差突然一巴掌,老汉顿时一个趔趄,后退一步,众人看得真切,这个公差正是刚才调戏妇女的那人,因父女二人未搭理他而有些羞恼成怒。
“官差大人为何打人?”
“打你?我还要抓你!”
“小人何罪之有,官差大人竟出此言!”
“我问你,你是不是安徽来的?”
“小民自安徽凤阳而来”
“最近李中堂大人正在安徽捉拿捻匪余孽,你父子二人,狼狈流窜到直隶,便有捻匪余孽嫌疑!”
老者面如土色,体似筛糠,豆大汗珠沁出额头,因紧张害怕竟说不出话来。
公差见老者不能说话,更加来劲,一把抓住老者炊帚般的发辫,胳膊一举就半拎了起来,老人顿时脚尖微微离地,面皮憋得暗红发紫,呼吸急促,好像就要要昏厥过去,女儿虽说也从安徽一路闯荡过来,但也没见过这等情景,吓得也说不出话来。官差还不肯干休,腾出手来,左右开弓,一口气打了老者十几个耳光,老者口鼻冒血,两眼发白,早已昏死过去。官差模样的人也似打累了一般,一把将老者掼在地上,伸手擦擦额头上的汗珠,从腰中就去摸官绳。
“住手!”宛如从空中打了个霹雳,张占魁一跃从店中越到当街,三两步走到老汉旁边,扶起老人,抱在怀里,从随身褡裢中摸出一个小瓶,拧开瓶塞,倒到手上几粒药丸,随手就喂老者吃下。只因当时,土匪盗贼也甚是猖獗,习武之风甚盛,保镖护院也经常会有些内外伤,所以,凡是习武之人,都会随身携带一些金创丹药药。迅速喂完老者,张占魁轻轻地将老者放在地上。站起身,转身像两个公差走来。两个公差见张占魁相貌不凡,有几分豪气,心上稍怯了几分。但公差的职业生涯练就二人喜怒不形于色的本领,只见二人抖了抖肩膀,扶了扶顶上暖帽,清了清嗓音,故意提高音调,大声问道:“这位汉子,你是何人?”
张占魁拱了拱手,道:“小可张占魁是也,二位公差大人何故将这老汉妇女一顿暴打?”
公差向来以欺压百姓为能,几曾被人这样质问,眼角眉梢多了几分怒气,但还是在脸上挤出几分笑容:“小哥有所不知,李鸿章李中堂大人正在皖北捉拿捻匪余孽,现已基本平定,捻匪作鸟兽散,此二人行动乖张,相貌可疑,我兄弟正欲带到府衙,听候知府梁大人大人审判。”
张占魁也是喝了几瓶白干,仗着酒劲,冲二人嬉笑道:“二位公差可是捻匪余孽?”
公差哪里被人这样调笑,怒气丛生:“你...................”
“我什么我,你看他俩像捻匪余孽,我看你俩还像捻匪余孽呢!无凭无据,莫须有的屎盆子,还是别往别人身上扣吧?我知道你俩是谁,不就是巡捕牛五的两个狗腿吗?我劝你俩还是多行好事,免得遭报!”
说完,回身扶起老人,架着向旁边不远的中医堂走去,女孩喏喏的跟在后边。
一个公差见张占魁出言如此不逊,便捋胳膊挽袖子,掏出官绳,想上前捆张
占魁,闪电手哪里把这两个烂番薯臭鸟蛋放在眼里,一个转身,把手一扬一扫,这个公差脸上便多了五条火辣辣的血印子。公差痛的赶紧撒手扔了官绳,两手捂脸,倒在地上,满地打滚。另一个公差见此阵势,哪里还敢上前招惹闪电手,一促一促的走到受伤公差旁边,扶起他来,连声的问:“三哥,三哥,你没事吧?”受伤公差忍住疼痛,拉着兄弟的手说:“兄弟,咱们快走,找五哥叫人去,这小子拒捕殴差,叫五哥带人来收拾他!快点扶我走!”说完,连个公差也不顾众人嬉笑,连掉在地上的官绳也没敢拿,一溜烟的像河间县城方向跑去。众人也自哄笑着散去。
翻回头再说张占魁,扶着卖艺老汉走进旁边的守珍堂,书中暗表,这守珍堂是河间府最著名的中医堂,坐诊郎中是金代名医刘完素二十八代玄孙,人送雅号“妙手回春刘一针”。如今刘郎中四十余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面色沉稳,一身正气。刘郎中正在坐诊,忽然见外边一个少年背进一个花甲老者,之间老者口鼻蹿血,面色蜡黄。一看便知受伤严重,生命垂危。出于医者仁心,刘郎中健步上前,轻轻的将老者从张占魁背上放下来,利索的扶到床上,从袖中掏出一颗银针,手指一捻,便扎入老者大椎穴,帮老者止住鲜血,随手又给老者灌入两粒金创还命丹。然后给老者盖上薄被,顺势把老者手腕一翻,开始号起脉来。只见刘郎中面色凝重,眼皮低垂,没有一丝面部表情。
片刻之后,刘郎中抬起手来,缓缓地走到脸盆前,轻轻地洗了洗手,然后又回到诊桌之前,双目低垂,若有所思。
张占魁和少女站在刘郎中旁边,过了一会,才诺诺的问:“郎中,你看这老丈的伤怎么样了?”
刘郎中缓缓抬起眼皮,缓缓道:“老人已是风烛残年,加上长时间食不果腹,衣不避寒,又是是受人欺凌,刚才我摸老丈的肚子,已是又硬又鼓,想必是老汉性格刚烈,但为了他人,忍辱偷生,心中憋闷了许多怨气所致。想是已灯枯油尽,再受了这番毒打,我已把他七窍封住,片刻之后,便会醒来!”姑娘和张占魁听后喜出望外,正欲答谢刘郎中,只听刘郎中继续说道:“醒来只能清楚片刻,唉,还需准备后事啊!”姑娘听后,伏在父亲身上嚎啕大哭,如此一个女子,流落他乡,无亲无故,受尽颠沛流离,受人欺凌之苦,如今相依为命的父亲又祸死他乡,连个裹尸的席子也不能置办,不由得悲从中来,嚎啕大哭。直哭得“寸寸柔肠连
肝断,盈盈粉泪汇腮边”。
第二章:静海县卖艺求果腹小南河施恩收少年第三章:闪电手二次学武艺霍元甲仗义烧烟馆第四章:师兄弟避难走唐山大力士摆擂霸天津第五章:大力士拳击伤老叟闪电手行侠救姑娘第六章:老叟临终赠秘笈姑娘伤愈刺洋人第七章:闪电手立约救姑娘,王子斌仗义收高徒第八章:天津卫同门聚会,斧头帮中日合谋。第九章:索天响津门祝寿,渡边雄宴会搅兴。第十章:玻璃花投日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