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1-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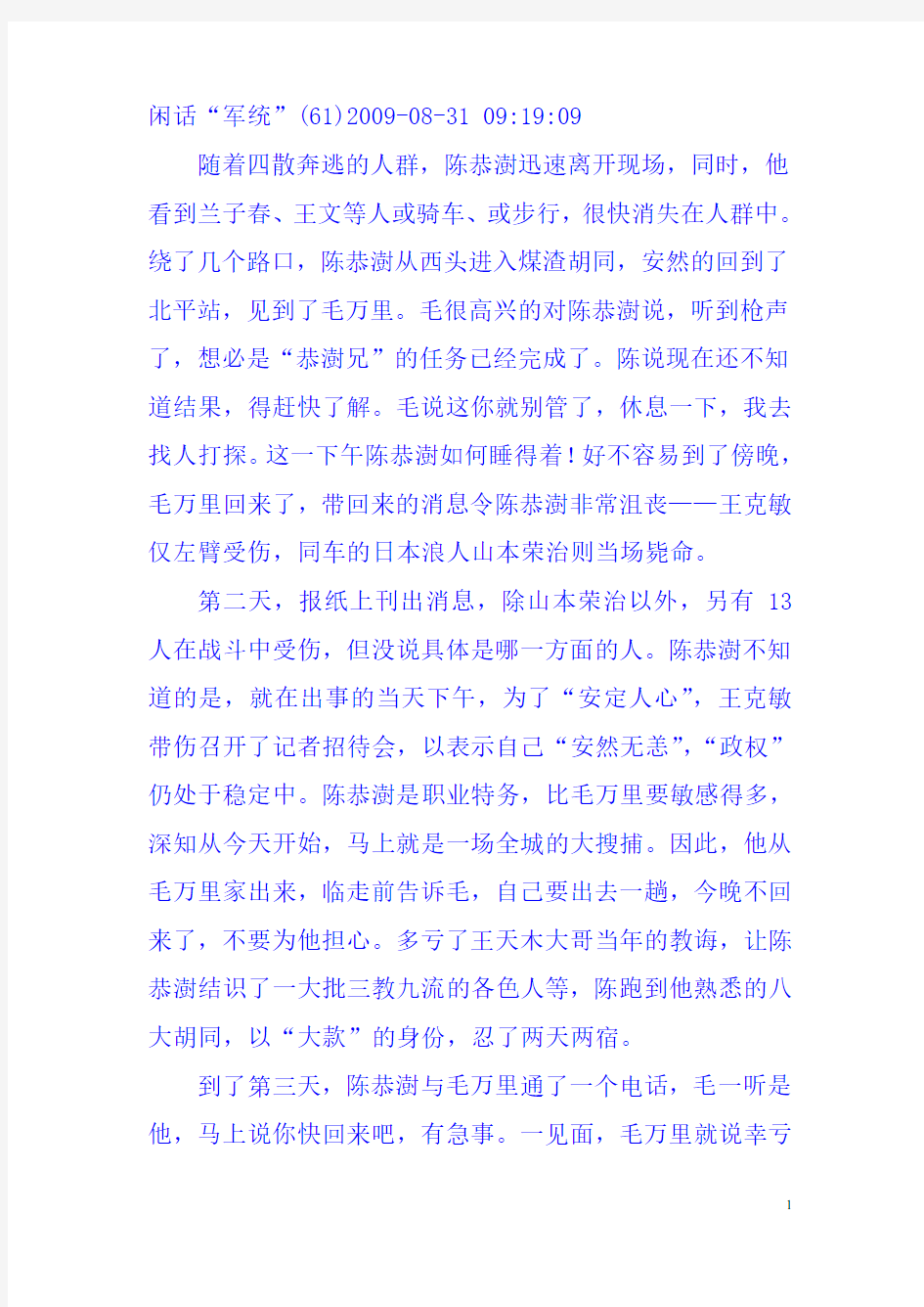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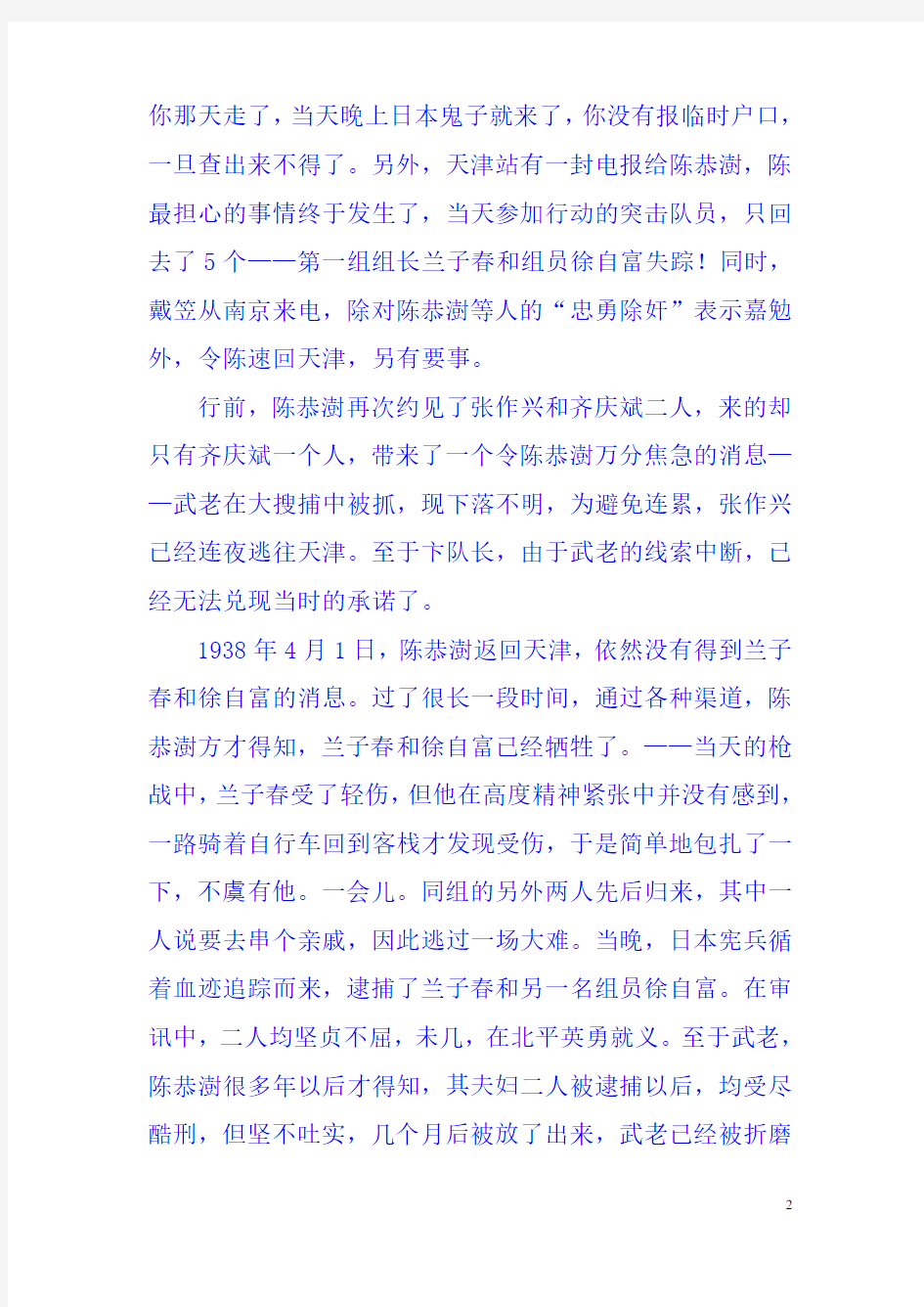
闲话“军统”(61)2009-08-31 09:19:09
随着四散奔逃的人群,陈恭澍迅速离开现场,同时,他看到兰子春、王文等人或骑车、或步行,很快消失在人群中。绕了几个路口,陈恭澍从西头进入煤渣胡同,安然的回到了北平站,见到了毛万里。毛很高兴的对陈恭澍说,听到枪声了,想必是“恭澍兄”的任务已经完成了。陈说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得赶快了解。毛说这你就别管了,休息一下,我去找人打探。这一下午陈恭澍如何睡得着!好不容易到了傍晚,毛万里回来了,带回来的消息令陈恭澍非常沮丧——王克敏仅左臂受伤,同车的日本浪人山本荣治则当场毙命。
第二天,报纸上刊出消息,除山本荣治以外,另有13人在战斗中受伤,但没说具体是哪一方面的人。陈恭澍不知道的是,就在出事的当天下午,为了“安定人心”,王克敏带伤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以表示自己“安然无恙”,“政权”仍处于稳定中。陈恭澍是职业特务,比毛万里要敏感得多,深知从今天开始,马上就是一场全城的大搜捕。因此,他从毛万里家出来,临走前告诉毛,自己要出去一趟,今晚不回来了,不要为他担心。多亏了王天木大哥当年的教诲,让陈恭澍结识了一大批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等,陈跑到他熟悉的八大胡同,以“大款”的身份,忍了两天两宿。
到了第三天,陈恭澍与毛万里通了一个电话,毛一听是他,马上说你快回来吧,有急事。一见面,毛万里就说幸亏
你那天走了,当天晚上日本鬼子就来了,你没有报临时户口,一旦查出来不得了。另外,天津站有一封电报给陈恭澍,陈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当天参加行动的突击队员,只回去了5个——第一组组长兰子春和组员徐自富失踪!同时,戴笠从南京来电,除对陈恭澍等人的“忠勇除奸”表示嘉勉外,令陈速回天津,另有要事。
行前,陈恭澍再次约见了张作兴和齐庆斌二人,来的却只有齐庆斌一个人,带来了一个令陈恭澍万分焦急的消息——武老在大搜捕中被抓,现下落不明,为避免连累,张作兴已经连夜逃往天津。至于卞队长,由于武老的线索中断,已经无法兑现当时的承诺了。
1938年4月1日,陈恭澍返回天津,依然没有得到兰子春和徐自富的消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通过各种渠道,陈恭澍方才得知,兰子春和徐自富已经牺牲了。——当天的枪战中,兰子春受了轻伤,但他在高度精神紧张中并没有感到,一路骑着自行车回到客栈才发现受伤,于是简单地包扎了一下,不虞有他。一会儿。同组的另外两人先后归来,其中一人说要去串个亲戚,因此逃过一场大难。当晚,日本宪兵循着血迹追踪而来,逮捕了兰子春和另一名组员徐自富。在审讯中,二人均坚贞不屈,未几,在北平英勇就义。至于武老,陈恭澍很多年以后才得知,其夫妇二人被逮捕以后,均受尽酷刑,但坚不吐实,几个月后被放了出来,武老已经被折磨
得“不复人形”,不久即含恨去世,其年轻的妻子则不知所终。“王克敏”案到此为止。虽然多有损失,但平心而论,在危机四伏的敌后,陈恭澍等不顾个人安危,以拼死一搏的勇气,狙击汉奸,不失为豪杰之举。
此战过后,陈恭澍“辣手书生”的名号不胫而走,好比逍遥津大战之后的张辽,华北群奸,“闻其大名,小儿不敢夜啼”。7年之后的1945年12月5日,时任军统局北平站督察的齐庆斌亲自拘押了王克敏,为自己的铁哥们陈恭澍出了一口恶气,同时被逮捕的还有殷汝耕等汉奸共14人。1945年12月 25日,王克敏因鸦片烟瘾发作死在狱中,这样一个恶名昭彰的人物,居然被他逃脱了“显戮”,实在是不公平。陈恭澍的故事,暂时只能写到这里,因为再往下已经进入全面抗战时期,而特务处也在1938年改建为军统局,但此前的许多事情还没有讲,如果顺着陈恭澍的事情一路讲下去,等再回头说其他事情的时候,读起来难免会有一种时空倒错的感觉。因此,为了叙事上的条理性,陈恭澍的故事暂且打住。
很佩服陈恭澍的抗日锄奸的勇气,但一直觉得他徒有虚名,勇猛有余,机智周全不足,由他主管的重大行动无一成功,(正如楼主所言张敬尧”案出自王天木,而上海站的一些行动多出自于下面的行动组,与当时并不熟悉上海的陈恭澍并无太大关系,他本人亦不否认),重大行动运气也很重
要,但那么多大行动无一成功显然说不过去。个人分析:一是陈的军事能力太差,虽出自黄埔,但显然没有好的军事素养,毕业后带兵剿匪都输得一塌糊涂,军事能力弱给他后来搞行动造成一些困难;二是过于年轻挑重担,他很早就得到戴笠的重视,但他的历事太少,显然不足欲应付大的行动,但戴笠拔苗助长。但我觉得他也有他的优点,就是比较虚心,善于团结人,从这点上看又有点少年老成的味道----谢军
闲话“军统”(62)2009-09-02 13:30:50
"郑苹如案"
郑苹如是牺牲在四十年代上海秘密战中许许多多烈士中的一位。郑苹如生于1918年,父亲郑钺曾留学日本,娶了一位日本太太,所以郑苹如是个混血儿。郑钺与中统特务陈宝骅(陈是陈果夫、陈立夫“二陈”兄弟的堂弟)是很好的朋友,由于这个关系,郑苹如与陈宝骅也走得很近,后来成为中统特工,并接受了刺杀丁默邨的任务。
按:以上是较为大众的说法,笔者认为,郑苹如究竟是不是中统特工,还有疑问。个人倾向于郑是基于民族义愤,主动请缨刺杀丁默邨的。
刺杀的经过,网上材料很多了,大体是抄来抄去,每抄一次,佐料就多一些,戏剧性就多一些,还着意加上了某些"香艳"色彩,什么某特务爱上她,到行刑时下不去手等等。把苏妲己的故事都安到郑苹如身上了。说这些话的人,我只能
说他们既无人心,也无脑子。所以这些不再赘述,大家只要知道郑苹如是抗日先烈就行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郑被捕后,汪伪当局曾找到郑的父母,说可以释放郑苹如,以此要挟郑铖出任伪职,其父母均严词拒绝。这叫精神!这叫气节!1940年2月,郑苹如烈士在上海从容就义,行刑的就是军统叛徒、刽子手林之江。次年,郑苹如的父亲郑铖因思念女儿,抱恨而终。1944年1月19日,郑苹如的弟弟、空军飞行员郑海澄在保卫重庆的空战中牺牲。1944年8月7日,郑苹如的未婚夫、郑海澄的战友王汉勋在执行任务时牺牲。郑苹如一家,可谓满门忠烈!1966年,郑苹如的母亲木村花子在台湾辞世,享年80岁。蒋介石亲题挽联“教忠有方”。郑苹如出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色戒》,其故事原型被认为取材于“郑苹如刺丁案”,这大家都知道了。郑苹如的妹妹郑天如曾公开抗议,并呼吁大家“切勿把片中沉溺情欲无法自拔的女主角,与历史上大义赴死的抗日烈士郑苹如画等号”。
张爱玲是否画了“等号”不重要,关键是我们不要去画这个等号就是了。另外,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色戒》的原著,如没看最好看一下,因为李安加了很多自己的东西进去。既然说到这了,就再说几句张爱玲。张爱玲是抗战期间躲在“孤岛”上海弄文学的一个,当时像她这样的作家有一批,出于这个原因,解放以后,张爱玲的作品也不太受人关注。张爱
玲“暴红”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连带着她那个汉奸情人胡兰成。要说谈世界观,以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张,那显然是两股道,没法谈。但即便以当年而论,至少要说张爱玲这个人,起码是民族意识不够鲜明吧。国家都这样了,还有闲情逸志风花雪月,还讽刺某个女作家长得好不好看。不怎么样!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是李鸿章的女婿,所以张爱玲多少有点贵族血统。弄得眼高于顶,一般的人是瞧不上的。
按:张佩纶属清末的“清流派”,这一派都是翰林,大都属于那种志大才疏的人,今天骂这个,明天损那个,就一样,没有什么实际工作的能力(张之洞是个例外)。让他们去负实际的责任,一定锛事。张佩纶就是这么个人,整日里大言不惭,满朝文武就没有一个他看得上眼。结果被人下了套,在中法战争中(1884年)被派到福建督战。这些人哪会这个,吹牛是可以的,打仗是不会的,结果打败不说,他自己还闹个临阵脱逃,丢人丢到了家!
笔者不太喜欢张的作品,应该说运用文字的能力还是挺纯熟的,但一味地哀婉绮靡,气象不高。既然说到张爱玲,就不能不说胡兰成,这个男人对张关系太大了。对此,许多人不免腹诽:你张爱玲爱谁不好,偏要爱一个汉奸;爱也就罢了,还爱得死去活来。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似乎天生就招女人喜爱。我们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朋友,或者认识这样的人,本人其貌不扬,也不一定有多高的社会地位、也不见得
多有钱、也没见啥大本事,就是找女人一门灵。今天找一个,明天换一个,女人跟了他好象还挺美,拣了个宝似的。这个,只能解释为——这种人的“性商”比较高、他身上从骨子里渗透着一种吸引女性的东西。没辙,这个不是生气的事。你有本事,但你找不着对象。胡兰成就是这么个人,而且他的“性商”可以说高到了极致,接近无与伦比的程度。更厉害的,胡兰成有才。
胡是个大才子,典型的江浙才子。关于胡的情事,大家去看《今生今世》就行了,没看过的网上有,这里就不多说了。胡兰成在海外名气很大,尤其是日本。他涉猎很广,不光会写散文,还是个学问家,其学说是成体系的。但我认真看了的只有《今生今世》,感觉也是那种腻腻歪歪、粘粘呼呼,不爱看。这里只就他当汉奸的经历,简单介绍一下。
胡兰成是浙江人,燕京大学肄业。1939年,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成立所谓“中央党部”,胡任其机关报《中华日报》总主笔。1940年—1941年,还曾兼任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宣传部政务次长(即常务副部长),后因卷入伪政权的派系斗争,不但给撤了职,还关了些日子。这就是胡兰成的汉奸经历,满打满算三年,时间不长,但足以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1944年,胡在上海认识了张爱玲,1947年分手,也只有三年,但足以影响张的一生。凡跟了胡的女人,鲜有时间长的,唯一的例外是最后一任太
太佘爱珍。按,佘爱珍的前夫吴世宝,原来是上海滩的一个“小猪猡”,后来成势,并参加“76号”,成为汉奸,以后我们会提到他。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胡兰成潜逃到老家浙江,并辗转于上海、香港等地,1950年前往日本定居。1974年—1975年,胡兰成曾有一个很短的时间到台湾任教,但终因观感太坏,被轰回日本。当时台文化界曾有人撰文《汉奸胡兰成速回日本去!》1981年,胡在日本去世,终年75岁。这样一个于公理、于私德都有所亏欠的人,居然得享高龄善终,也算奇事一桩。
有太多的非中共方面的爱国志士,尤其是抗日志士被掩盖了,作者能够把这些英烈的事迹讲出来,实在是功德无量!小时候我就一直有困惑——历史书上总是说八路军装备特别差,而侵华日军有又常凶残且武器精良,这么厉害的鬼子怎么会被如此弱的八路军打败呢?
闲话“军统”(63)2009-09-03 13:49:11
“中央党部刺汪”案
汪精卫这个人一生经历极为丰富,撇开最后当汉奸不说,前半生,端的是丰富多彩。比如,汪精卫虽然是一介书生,却曾经当过刺客、也曾经遇刺,而且遇刺一回还不够,还要来个两回。当刺客的那一下,就此奠定汪精卫一生的革命本钱。遇刺的两回,第一回有点冤,第二回可是咎由自取。然而,最终真正要了他的命的,却是第一次、即今次要说的
“中央党部刺汪”案。谈到汪精卫,真的有一种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这么老资格的一位“革命家”,最后居然落水当了汉奸,想起来都替他惋惜。不过,这也是他长期亲日的必然结果,否则,不至于在中央党部替他“一生的政敌”蒋介石挨枪子儿,所以说冤也不冤。
按:在国民党内部,乃至往前回溯到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等等,其高层人士中,相当多的人都有深厚的日本背景,首先就是中山先生。更有大批的留日学生,如黄兴、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戴季陶、阎锡山、何应钦、白崇禧,等而下之的,包括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殷汝耕、王克敏,军统内部的王天木等等,就更多了。我们前面说了,之所以八年抗战中会出现那么多汉奸,与当时政界的中、上层有一大批亲日派,有直接的关系。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实际上是此后不久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会议。会议地点在南京中央党部大院。第一天会议的程序是:
8点:与会人员到中山陵“谒陵”,然后回到中央党部;
9点:准时进行大会开幕式,听汪精卫做报告;
开幕式结束后,大家在院里照合影;
10点半开始大会的预备会议。
当天,蒋介石于8点前到达“总理陵堂”,结果蒋发现
他居然是来的最早的。过了8点,“中委”们才陆续来到,而且许多人很不严肃,没有按事先的通知要求着礼服,穿中山装的、制服的都有,居然还有人穿着便装就来了。蒋介石非常生气,但碍于正置身中山先生陵园,不便发作。8时20分,谒陵仪式结束,蒋介石一怒之下,把他事先定好的讲演也取消了,坐上车就走。在返回中央党部的路上,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一辆出租车从后面很快地追上来,在超车的过程中,还有人从窗户里探出头来往回看。蒋介石发现了,觉得不对头,于是叫慢点开,让出租先过去。开了一段,赫然发现那辆出租居然停在路边等着他们,蒋大怒,令人下去盘问,一问,对方说是记者。一个记者的车、还是辆出租,敢超蒋介石的车队,还窥视、守候,想干什么?但问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来,总不能因为超了你的车就抓起来吧,只得作罢。
回到中央党部举行四届六中全会的开幕式,由汪精卫致开幕词。原来拟订的开会程序,依照以往的惯例,有“默念总理遗瞩”一项,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主持人把这一项漏掉了,汪精卫在意外的情况下,提前上台致开幕词:“我们这几年,看见了各位同志的努力,其中如‘剿匪’之努力,已得到极大的成绩。其他建设,也得到若干成绩。但这种成绩,并不能使我们得到满意和安慰,就是因为国难并没解除,而且更加深重……,我们决心以无限的勇气,来负担这责任,以谋国难之解除”。
由于意外的变故,据陈公博后来回忆,著名的“演讲专家”汪精卫,当天的表现极为失常,“声音颤抖、脸色苍白”。汪精卫的开幕词很短,只有20分钟就结束了,大家下楼来到门前的台阶上,分成五排准备合影。正中,自然是蒋介石和汪精卫,第一排的还有林森、张静江、孙科、戴季陶、阎锡山、张学良、张继等等。除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因患病行动不便,给他设了一张藤椅之外,其他人都是站着。大家都排好了,蒋介石却迟迟不露面,汪精卫让蒋的侍卫长王世和去请蒋“莅临”,等了半天还是没来。汪精卫只好亲自去请。蒋说,今天秩序太乱,我觉得要出事,我不去了,你也不要去。
蒋不愧是军人,第六感官很灵敏。汪精卫则不以为然,说这么重要的场合,咱俩都不去不太好。说了半天,蒋就是不动地方,汪精卫只好自己出来,站在中间。记者们对着第一排围成一个半圆形,嘁哩咔嚓一通闪光,9时35分,摄影完毕。汪精卫正准备转身,此时突然一个记者跳了出来,高呼“打倒卖国贼”,随即掏出手枪,冲着汪精卫就是三枪,汪应声倒地。以事出突然,大家都惊得目瞪口呆,平日里不苟言笑的衮衮诸公,此时都露出了原型。据陈公博说,张静江“滚到地上”,孔祥熙居然“钻到汽车底下”。这个时候——挺身而出的,居然是文人张继。
闲话“军统”(64)2009-09-04 12:01:19
张继,与唐朝某著名诗人同名,1882年生,河北南皮人。
这个南皮是个很有名的地方,晚清名臣张之洞祖籍就是这里的人。张之洞是同治二年恩科的探花;他的堂兄张之万更了不起——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丁未科状元,这两科都很出名,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丁未科厉害,并不是因为张之万这个状元,而是因为这一科出了个李鸿章,不过当年他的名次比张之万可差远了——二甲第十三名进士!同治二年恩科的状元叫翁曾源。翁曾源是翁同龢的侄子,著名的“叔侄两状元”传为佳话。翁曾源患有“羊角风”,一发病就口吐白沫、人事不知。事有凑巧,正好殿试那天精神抖擞,把张卷子答得无懈可击,一举抡元。所以,和张之万那一科相同,同治二年恩科也不以状元闻名,出名的是探花张之洞。
从二张兄弟起,南皮文风大盛,张继就出生在南皮的一个世家。1899年,张继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经济。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遂“投身革命”。后来,因与邹容等强行剪去留日学生“监督”姚文甫的辫子,张继被驱逐回国。回国以后,张继与黄兴创立华兴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纲领,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作为国民党元老,张继成为与胡汉民、汪精卫、张璧齐名的“南胡汪、北二张”之一的人物。辛亥革命以后,张继任国民党北方执行部负责人,李大钊同志就是由张继介绍加入国民党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张继是故宫博物院的创始人之一,为故宫博物院的创立以及重要文物的保全起到过重要作用。但
他与另一位国民党元老、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易培基不大对付,时有龃龉,到最后居然出以政治手段,结果弄出了“故宫盗宝”的惊天大案,易培基竟至抱恨而终。其中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隔了多年之后,依然是各执一词,政治家的政治手腕,原不是我们这些晚生后辈可以置喙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参看吴祖光先生的父亲吴瀛老先生的《故宫尘梦录》。
关于张继,有很多话题,比如他的“惧内”、比如他家公子闹出的那桩很出名的命案,奈何离题万里,不说也罢。但有一点必须要说,张继是一个极有胆识、有担当的人。1904年,华兴会在长沙组织暴动失败后,张继作为一个书生,曾“手持双枪”,冒死护送黄兴突围。l947年,张继病逝于南京,葬于北京万安公墓。扯远了。却说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被刺,当时已经53岁的张继,奋不顾身地扑了上去,从背后死死抱住了年轻力壮的刺客,旁边的张学良上去一脚将刺客手中的左轮踢飞。这时,汪精卫的卫士才赶到,两枪将刺客打成重伤。枪法还真不错——这么近的距离,居然没伤着张继。最先赶到出事现场的,是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此时汪精卫自忖必死,于是说:我为革命,死而无憾。
陈璧君是一个性格非常刚强的人,生死关头面前丝毫不露小女子态,只是说:“四哥(汪在家里行四),你放心吧,你死后有我照料儿女。革命党反正要横死的,这种结果我早
已料到。”这时蒋介石也赶来了,汪精卫对他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以后的责任,要你一个人来负了。”蒋介石一条腿半跪下来,握住汪精卫的手说:“不要紧、不要紧,不要多说话。”陈璧君也是“老革命家”了,当年曾“毁家纾难”,在国民党内很有声望,论资格还老于“后起之秀”蒋介石。因此毫不客气地对蒋说:“蒋先生,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可以不干,何必用这种手段!”
几句话说出来,抢白得“蒋先生”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心里“搓火”又不便发作。据陈公博回忆,当时还是他亲自给中央医院打的电话,说了半天,对方才肯出诊。医生半天不来,汪精卫就那么躺在地上,蒋介石和陈璧君就那么站在旁边等着,另一边还躺着一个刺客。——要说这事也够新鲜的,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出了这么大的事,医院居然还敢推三阻四,今天的我们,真是不可理解。这时,大家忽然发现孔祥熙“失踪”了。找了半天才发现孔祥熙在汽车底下,出不来了——进去的时候出以慌乱,多小的“空”都能钻进去,出来可就不行了。找了几个人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拽出来,把马褂的袖子都给拽撕了。
检查结果,汪精卫身中三枪——刺客一共就开了三枪,由于是抵近射击,三枪全部射中,而且还有“绝”的——刺客开枪的一瞬间,汪精卫正在转身,因此这三枪,有从后面打进去的,也有从前面打进去的、还有从侧面打进去的,你说这
三枪挨的,一点不糟践。后面的一枪最轻,打穿了左上臂,属于贯穿伤,处理一下伤口即可。前面的一枪就有些麻烦,射进左眼外角下颧骨(我博客里有照片),做了三次手术,才把把子弹取出来。问题最大的是侧面的一枪,从右背射进,可是子弹却怎么也找不到。没办法又送到上海一家法国人办的医院,结果发现子弹正好卡在肋骨上,伤及脊椎。以当时的医疗条件,医生认为取出子弹难度很大,且有生命危险,建议保守治疗,用药物控制,并保证30年不会出问题。——殊不知,9年之后,正是这颗子弹,要了“汪逆精卫”的命。
闲话“军统”(65)2009-09-09 17:50:52
与汪精卫同时被送到医院的还有刺客,当时,卫兵们从他身上搜出一张“晨光通讯社”的记者证,姓名是孙凤鸣。另外,只搜出一颗用于自杀的鸦片烟泡和六角钱,可见刺客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做这件事的。汪精卫被刺,日子难过的却是蒋介石。用陈公博的话说,大家都怀疑这件事是蒋先生的特务队干的。“蒋先生的特务队”是蔑称,指的就是戴笠的特务处。想想也正常,谁都知道“蒋先生”和“汪先生”不对付,汪先生遇刺,那不是蒋先生干的还有谁?别人谁有这么大胆子?再说了,照相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出席,显然是事先就知道有事要发生,再明显不过了。
其实,这件事真是冤枉了“蒋先生”。试问,蒋介石要
刺杀汪精卫,在哪儿不行,非得在中央党部?什么时候不行,非得在中央全会开会的现场?蒋介石怎么会干这种蠢事?无奈这种事无法辩白,说了别人也不会相信,蒋介石“哑巴吃黄连”,背了个天字第一号的巨型黑锅。要想撇清自己,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破案。据说当时蒋介石就把戴笠叫来痛骂了一顿:“人家都打到中央党部来啦!每月几十万元法币给你们,就为酿出这等祸事吗?”当天,一向冷静、讲究风度的蒋介石,居然用冷水冲头,可见“搓火”到了极点。确实,一个国民党的“中常会”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常委(不要说还是国府的“行政院长”),居然在自己家里被人行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都是一个笑话。既然是“笑话”,就有人在等着看结果。
有的记者去采访国府主席林森,林说:“外边的事,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是替蒋先生掌印把子。”还有记者去问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吴“顾左右而言他”,说:“我是无锡人,无锡有108个烟囱,全国都像无锡,做到实业救国就好了。”当然了,也有一些人颇为关心——都是些吃特务饭的。宪兵司令谷正伦找到桂永清商议,怀疑是康泽他们干的。陈立夫也在自己的内部进行追查,他手下不是也有个特务机构么——叫“中央党部调查科”的。当天下午,蒋介石召集相关人员开会——都是形形色色的特务——有陈立夫、有宪兵司令谷正伦、有教导总队长桂永清、有黄埔同学会刘健群,
还有复兴社的贺衷寒、康泽、邓文仪等等。
蒋介石大发脾气,又提起他今天从陵园到中央党部路上遇着记者出租车的事说了一遍,指责宪警工作失误,要求抽调得力人员参与侦破,经费由军政部拨用,限一星期查出头绪,一个月内破案,否则,今天到会的人全部撤职查办。总之,不惜人力物力,必须早日破案,“以正视听”。蒋介石还要求,每天要派人去中央医院探望汪精卫伤情,并向他汇报情况——其实,探病是一方面,关键是看看都是些什么人在往医院跑、谈些什么、是不是又在往我身上“泼污水”!
确实,汪精卫一出事,中央医院立马变成了“临时中央党部兼行政院”。汪精卫不是一般领导,出了事,大家都得拎着东西去看。不要说还有各种各样的人士抱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往医院跑,有的是探病的、有的是看情况的,陈璧君安排人接待,忙得不亦乐乎。蒋介石特地请各派系首脑代表他前去看望汪精卫,同时侧面向陈璧君解释:“这事真不是蒋先生派人干的,保证限期破案。”云云,并请陈壁君派人参加侦破,以示坦白。
次日,汪案特别侦查处成立,下设4个组:
第一组是戴笠的特务处;
第二组由教导总队桂永清负责,以教导总队中的复兴社基层骨干为主;
第三组由宪兵司令部谷正伦负责,由宪兵、中央军校中的复
兴社基层干部组成;
第四组由中央党部负责。
在特务处召开的汪案特别侦查处成立大会上,与会者对案情进行了分析。军校八期毕业生吴幼元,当时在教导总队任职,参与了侦破。据他回忆:大家分析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情况:
“国内方面:
共产党:经过长期作战,伤亡惨重,只求整补自安,不会寻找麻烦,也不会采用刺杀个人手段。
民主党派:没有这样大的魄力和胆识出此下策。
国民党内部:胡汉民的两广集团,目前政治、经济都很困难,不会向中央挑衅。
地方势力:如山东韩复榘,也只是与日本人暗中勾结,已派部队进行监视,不可能刺汪。如云南龙云、四川刘湘、贵州王家烈,以及西北地方实力派,虽对中央怀有二心,但与汪无宿怨。
国际方面:
意大利帮我建设空军,但又与日本互通情报,出于某种动机,刺汪或有可能。
德国情况和意大利一样,一面助我训练新军,一面又偏袒日本,曾卖军火给西北地方实力派,反说中国人不争气,有可能参预刺汪案。
俄国人(当时对苏联通称)是第三国际总部,企图中国赤化,经常在边界挑衅,阻碍中国统一,但不会采取暗杀手段。日本,侵占我东北四省后,网罗汉奸,进行颠覆活动,是最大的敌人,很可能收买亡命之徒,进行暗杀、破坏活动。”
但以上说的都是可能,没有任何证据,目前,唯一线索应从孙凤鸣和晨光通讯社入手。问题是——孙凤鸣已经死了。
闲话“军统”(66)2009-09-14 20:23:45
遇刺当天,汪精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窃思本人生平并无私仇。而最近数年,承乏行政,正值内忧外患重重煎迫之际,虽殚心竭力,而艰难周折,外间何从得知?倘因此误会,致生暴举,于情不可无原。拟恳请国府,将牵连犯人从宽赦免。”然而,汪精卫的慈悲心肠已经无济于事。孙凤鸣所中的两枪都在胸部,送到医院时已经奄奄一息,为了掏出口供,特务命令医生尽全力抢救,即便如此,孙凤鸣始终处于昏迷状态,于11月2日凌晨3时许死亡。其间,孙曾在弥留之际说了“中央军校”、“姓张的”等几个词,其他的就什么都没有了。根据这唯一的线索,特务们把目光集中到了“中央军校”。所谓“中央军校”,其实就是当年的黄埔军校——1928年,蒋介石以中央军事委员会名义,将已经迁到南京的黄埔军校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按:从“黄埔军校”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其实远
不是一句话那么简单,热闹着呢,最极端的时候,在武汉、广州和南京同时出现了三个“黄埔军校”。这事,以后讲“黄埔军校”的时候再说。
中央军校的教职员工及学员有4000多人,特务们大海捞针一般地挨着个核对,最后列出十多个姓张的作为嫌疑人。其中,特务们发现有一个有少尉张某比较可疑。张某是安徽合肥人,二十五、六岁,由于其妻没有工作,生活比较拮据,但一个多月前,张家忽然雇了一个佣人,其妻还添置了不少新衣服,其消费水准与收入水平明显不相称。另外,其妻有时几天不归,行迹亦有可疑之处。当时中央军校教育长是张治中,特务们在未向校方通报问题的情况下,秘密拘捕了张某夫妇,并进行隔离审查。
前面我们曾经说过,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夫妻双方同时被捕,因为分别询问,两下一凑,破绽立现。经过对张某两口子的讯问,发现双方供词彼此矛盾、互相出入之处颇多,如介绍人、结婚时间、地点,都对不上号,立即将张某夫妻关押起来。另外派了两个特务假扮夫妻住进了张家,守株待兔,等着有人来自投罗网。果不其然,11月3日夜,接到上海来的一封电报,内称“母病速归”四个字。特务们问张,张说母亲在合肥,上海没有亲戚。又问其妻,也说上海没有亲戚。——张某夫妻没有反侦察的经验,他俩是不知道上海有电报来,照实供认的。至此,特务们认定,此事必然与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