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笔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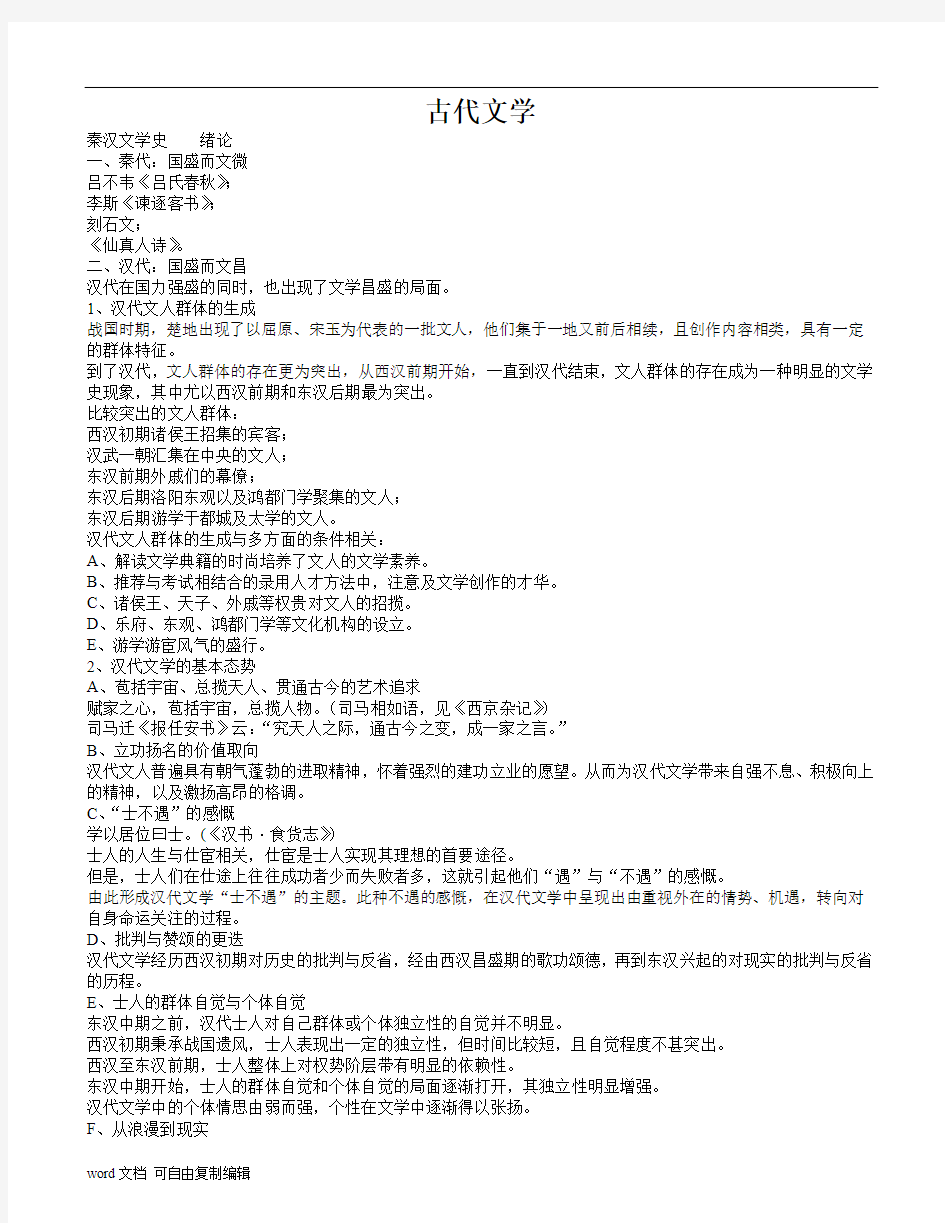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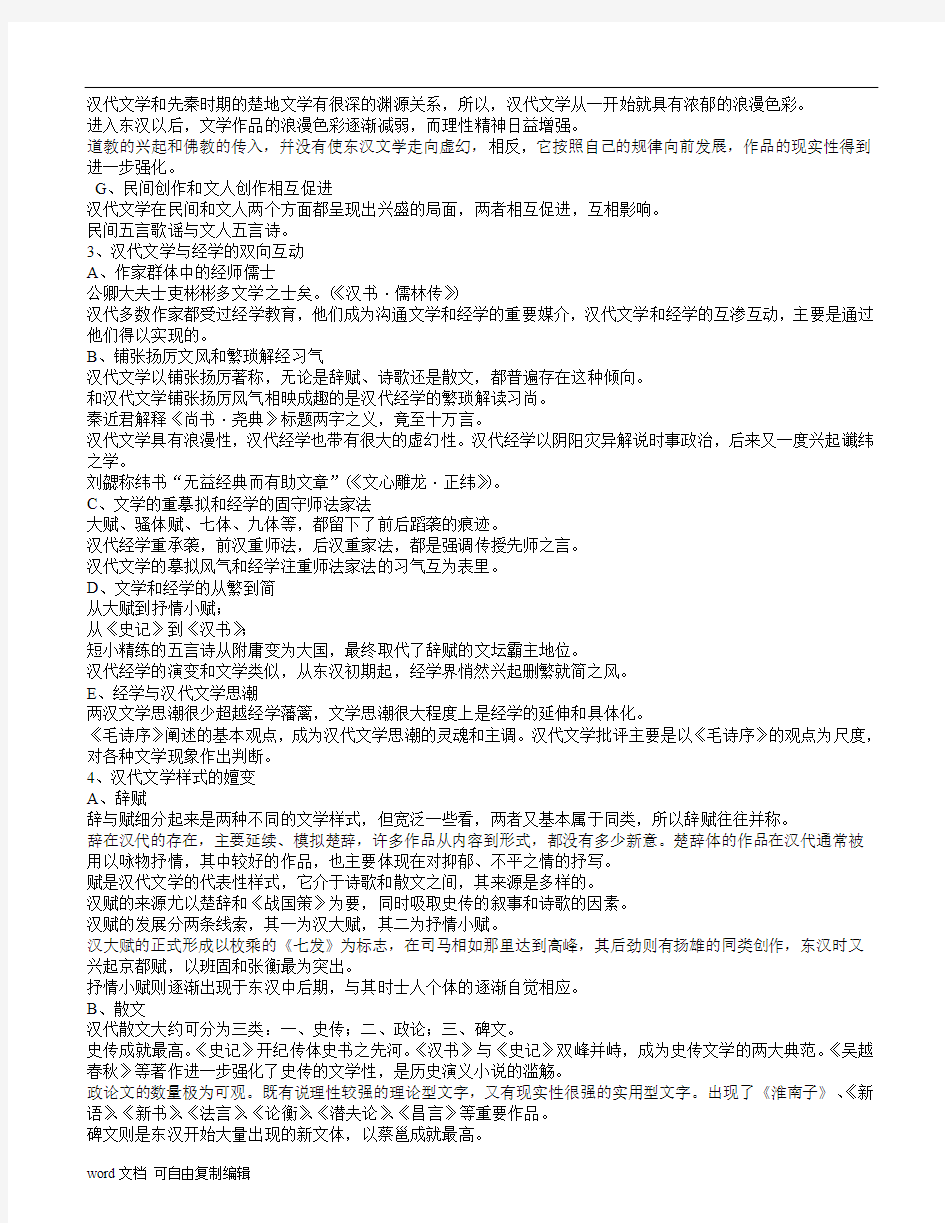
古代文学
秦汉文学史绪论
一、秦代:国盛而文微
吕不韦《吕氏春秋》;
李斯《谏逐客书》;
刻石文;
《仙真人诗》。
二、汉代:国盛而文昌
汉代在国力强盛的同时,也出现了文学昌盛的局面。
1、汉代文人群体的生成
战国时期,楚地出现了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一批文人,他们集于一地又前后相续,且创作内容相类,具有一定的群体特征。
到了汉代,文人群体的存在更为突出,从西汉前期开始,一直到汉代结束,文人群体的存在成为一种明显的文学史现象,其中尤以西汉前期和东汉后期最为突出。
比较突出的文人群体:
西汉初期诸侯王招集的宾客;
汉武一朝汇集在中央的文人;
东汉前期外戚们的幕僚;
东汉后期洛阳东观以及鸿都门学聚集的文人;
东汉后期游学于都城及太学的文人。
汉代文人群体的生成与多方面的条件相关:
A、解读文学典籍的时尚培养了文人的文学素养。
B、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录用人才方法中,注意及文学创作的才华。
C、诸侯王、天子、外戚等权贵对文人的招揽。
D、乐府、东观、鸿都门学等文化机构的设立。
E、游学游宦风气的盛行。
2、汉代文学的基本态势
A、苞括宇宙、总揽天人、贯通古今的艺术追求
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司马相如语,见《西京杂记》)
司马迁《报任安书》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B、立功扬名的价值取向
汉代文人普遍具有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怀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从而为汉代文学带来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以及激扬高昂的格调。
C、“士不遇”的感慨
学以居位曰士。(《汉书·食货志》)
士人的人生与仕宦相关,仕宦是士人实现其理想的首要途径。
但是,士人们在仕途上往往成功者少而失败者多,这就引起他们“遇”与“不遇”的感慨。
由此形成汉代文学“士不遇”的主题。此种不遇的感慨,在汉代文学中呈现出由重视外在的情势、机遇,转向对自身命运关注的过程。
D、批判与赞颂的更迭
汉代文学经历西汉初期对历史的批判与反省,经由西汉昌盛期的歌功颂德,再到东汉兴起的对现实的批判与反省的历程。
E、士人的群体自觉与个体自觉
东汉中期之前,汉代士人对自己群体或个体独立性的自觉并不明显。
西汉初期秉承战国遗风,士人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但时间比较短,且自觉程度不甚突出。
西汉至东汉前期,士人整体上对权势阶层带有明显的依赖性。
东汉中期开始,士人的群体自觉和个体自觉的局面逐渐打开,其独立性明显增强。
汉代文学中的个体情思由弱而强,个性在文学中逐渐得以张扬。
F、从浪漫到现实
汉代文学和先秦时期的楚地文学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所以,汉代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
进入东汉以后,文学作品的浪漫色彩逐渐减弱,而理性精神日益增强。
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幷没有使东汉文学走向虚幻,相反,它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作品的现实性得到进一步强化。
G、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相互促进
汉代文学在民间和文人两个方面都呈现出兴盛的局面,两者相互促进,互相影响。
民间五言歌谣与文人五言诗。
3、汉代文学与经学的双向互动
A、作家群体中的经师儒士
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汉书·儒林传》)
汉代多数作家都受过经学教育,他们成为沟通文学和经学的重要媒介,汉代文学和经学的互渗互动,主要是通过他们得以实现的。
B、铺张扬厉文风和繁琐解经习气
汉代文学以铺张扬厉著称,无论是辞赋、诗歌还是散文,都普遍存在这种倾向。
和汉代文学铺张扬厉风气相映成趣的是汉代经学的繁琐解读习尚。
秦近君解释《尚书·尧典》标题两字之义,竟至十万言。
汉代文学具有浪漫性,汉代经学也带有很大的虚幻性。汉代经学以阴阳灾异解说时事政治,后来又一度兴起谶纬之学。
刘勰称纬书“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文心雕龙·正纬》)。
C、文学的重摹拟和经学的固守师法家法
大赋、骚体赋、七体、九体等,都留下了前后蹈袭的痕迹。
汉代经学重承袭,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都是强调传授先师之言。
汉代文学的摹拟风气和经学注重师法家法的习气互为表里。
D、文学和经学的从繁到简
从大赋到抒情小赋;
从《史记》到《汉书》;
短小精练的五言诗从附庸变为大国,最终取代了辞赋的文坛霸主地位。
汉代经学的演变和文学类似,从东汉初期起,经学界悄然兴起删繁就简之风。
E、经学与汉代文学思潮
两汉文学思潮很少超越经学藩篱,文学思潮很大程度上是经学的延伸和具体化。
《毛诗序》阐述的基本观点,成为汉代文学思潮的灵魂和主调。汉代文学批评主要是以《毛诗序》的观点为尺度,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出判断。
4、汉代文学样式的嬗变
A、辞赋
辞与赋细分起来是两种不同的文学样式,但宽泛一些看,两者又基本属于同类,所以辞赋往往并称。
辞在汉代的存在,主要延续、模拟楚辞,许多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多少新意。楚辞体的作品在汉代通常被用以咏物抒情,其中较好的作品,也主要体现在对抑郁、不平之情的抒写。
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性样式,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其来源是多样的。
汉赋的来源尤以楚辞和《战国策》为要,同时吸取史传的叙事和诗歌的因素。
汉赋的发展分两条线索,其一为汉大赋,其二为抒情小赋。
汉大赋的正式形成以枚乘的《七发》为标志,在司马相如那里达到高峰,其后劲则有扬雄的同类创作,东汉时又兴起京都赋,以班固和张衡最为突出。
抒情小赋则逐渐出现于东汉中后期,与其时士人个体的逐渐自觉相应。
B、散文
汉代散文大约可分为三类:一、史传;二、政论;三、碑文。
史传成就最高。《史记》开纪传体史书之先河。《汉书》与《史记》双峰并峙,成为史传文学的两大典范。《吴越春秋》等著作进一步强化了史传的文学性,是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
政论文的数量极为可观。既有说理性较强的理论型文字,又有现实性很强的实用型文字。出现了《淮南子》、《新语》、《新书》、《法言》、《论衡》、《潜夫论》、《昌言》等重要作品。
碑文则是东汉开始大量出现的新文体,以蔡邕成就最高。
C、诗歌
主要是乐府诗和五言古诗。
五言诗开始主要见于西汉的歌谣和乐府诗,到东汉时,文人的五言诗创作也逐渐兴起,班固、张衡、秦嘉、蔡邕等人在这一方面有重大贡献。
五言诗领域出现《孔雀东南飞》这样的叙事名篇,以及《古诗十九首》这样抒情典范。
D、汉代文学的阶段性
高祖至景帝时期,多承战国余绪,而新的因素也在萌生之中。
武帝至宣帝时期,汉代文学自家面貌形成。汉大赋和史传都是与时代状况相称的典范之作,政论文也呈现出汉代经学笼罩下的自家风貌。
元帝至东汉和帝时期,守成地延续西汉以来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辞赋和史传方面,而政论文则出现分流,其一延续经学的影响而更显典正、规矩,其一出现反弹,批判精神得到张扬。
安帝至灵帝时期,文学面貌逐渐转变,文学中个体性的内容日渐突出,文人在文学作品中越来越多地关注“人”的生命、命运,同时对人生的价值进行新的思考,诗文日趋整饬华美,预示着一个文学自觉时代的即将到来。第一章
秦及西汉前期的散文和辞赋
第一节秦代文学
“车同轨,书同文”
“秦世不文”(《文心雕龙·诠赋》)
“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一、《吕氏春秋》
吕不韦
八览、六论、十二纪。
(“吕览”)
《吕氏春秋》的文学成就:
第一,体系严密。
十二纪(十二个月)
八览(八方、八极)
六论(六亲、六义)
第二,用事说理生动。
大量比喻、故事帮助说理
第三,寓言故事丰富多彩。
二百多则
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在,法虽今而在,犹若不可法。故释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一脬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
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坏都舍。向其先表之时可导也,今水已变而益多矣,荆人尚犹循表而导之,此其所以败也。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感乎?以故法为其国与此同。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有过于江上者,见人方引婴儿而欲投之江中,婴儿啼。人问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以此任物,亦必悖矣。
二、李斯《谏逐客书》
李斯
代表作品为《谏逐客书》
写于秦王政十年(前237)
郑国渠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
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
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悦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之无危,不可得也。
全文议论驰聘,气势奔放,比物连类,辞采斐然;既富有战国文章宏放雄辩的姿态,又开启汉代辞赋铺叙藻饰的特色,是一篇趋向骈偶化的政论散文,被后人誉为“骈体之祖”。
秦刻石文大多出于李斯之手。
《吕氏春秋》:
战国后期吕不韦组织门客编撰的一部历史著作。全书分八览、六论、十二纪三大部分,又称《吕览》。思想驳杂,文章多用故事说理,生动有趣。
第二节贾谊和汉初散文
一、陆贾《新语》
贾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贾曰:“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帝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以并天
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有惭色,谓贾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贾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称其书曰《新语》。(《汉书·陆贾传》)
二、贾谊
贾谊(前200—前168年),洛阳人。
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
18岁有才名;
20余岁被文帝召为博士;
后被破格提为太中大夫;
23岁时,被贬为长沙王太傅;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李商隐《贾生》)
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
死时年仅33岁。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坠马寻常事,何需哀伤付一生。(毛泽东《贾谊》)
所著文章58篇,刘向编为《新书》。
散文名篇主要有《过秦论》上、中、下三篇,《陈政事疏》(亦名《治安策》),《论积贮疏》等。
辞赋以《吊屈原赋》、《鵩鸟赋》为代表。
贾谊的散文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专题性的政论文。
如《过秦论》: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然而)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
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不直说秦之过,而先以奔放之言历举秦之功;
不径言秦之衰,而先以豪迈之语详述秦之兴;
不先写秦之亡,而先以昂扬之笔尽书秦之盛。
在纵笔泼墨绘足龙腾云卷之态后予以点睛: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二是针对各种具体问题有感而发的疏牍文。
《陈政事疏》及《新书》之“事类”。
此类散文的特色是观察敏锐,能透过各种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也就是说能够透过太平景象觉察到社会潜伏的矛盾和危机。
如《数宁》云:“曰天下安且宁者,非至愚无知,固谀者耳……夫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势,何以异此?”
三是利用各种历史材料和故事来说理的文章。
《新书》之“连语”、“杂事”。
《吊屈原赋》是赴长沙王太傅之职,路过湘水凭吊屈原时所作,是汉初骚体赋之代表。
《鵩鸟赋》是谪居长沙时所作,是一篇哲理赋。主要阐明作者对于生死、祸福的达观态度:“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
《吊屈原赋》:
谊为长沙王太傅,既以谪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其终篇曰:“已矣哉!国无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罗而死。谊追伤之,因自喻,其辞曰:
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讬(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没有准则)兮,乃殒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闒(tà小门)茸(r?ng小草)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
蹻(ju?庄蹻)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銛。吁嗟默默(不得志的样子),生(指屈原)之无故(《文选》注曰“无故遇此祸也”)兮;斡弃(斡w?:旋转。斡弃:抛弃)周鼎,宝康(空、破)瓠(hù瓦罐)兮。腾驾罢(p í疲惫)牛,骖蹇驴兮;骥
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古代的一种礼帽)荐(垫)履,渐(这里指时间短暂)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罹)此咎兮。
讯曰(告曰):已矣!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抑郁)其谁语?凤漂漂(飘飘)其高逝兮,固自引而远去。袭(效法)九渊之神龙兮,沕(mì隐
没)深潜以自珍;偭(miǎn面向)蟂(xiāo古书上说的水獭一类的动物)獭以隐处兮,夫岂从虾与蛭螾(蚓)?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般(久)纷纷(乱纷纷的样子)其离(罹)此尤兮,亦
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遥曾击(高翔)而去之。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横江湖之鳣(zhān鲟一类的大鱼)鲸兮,固将制于蝼蚁。借凭吊屈原来抒发自己的悲愤情怀。
此赋铺叙与议论并用。无论是铺叙,还是议论,都熔铸了作者的激愤情感,带有强烈的抒情色彩。
此赋模拟楚骚的迹象明显,尚处于汉赋早期创作由楚辞向汉赋的过渡状态。
《鵩鸟赋》:
谊为长沙王傅,三年,有鵩飞入谊舍。鵩似鸮(xiāo),不祥鸟也。谊既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也。其辞曰: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
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作品在抒发对人生、社会的感慨时,表现出鲜明的道家倾向。
汉赋:
是汉代新兴的独特文体,介于韵散之间。一般认为源于古诗,奠基于楚辞,形成和兴盛于两汉。汉赋是汉代赋体文学的总称,一般认为包括骚体赋、汉大赋和抒情小赋,但以汉大赋最为典型。
骚体赋:
指模仿屈原《离骚》等楚辞作品而写成的一种赋,内容上继承了楚辞的“怨刺”传统,抒写朝廷忠奸不分贤人失志,形式上大抵保持了楚辞整饬中见变化、情与辞相宛转的特点,常用带“兮”字的语句,如贾谊的《吊屈原赋》等。
三、晁错
颍川人。
早年学申、商刑名之学。
文帝时,被派往故秦博士伏生处接受《尚书》的传授。
历任博士、太子家令。深得太子(即后来的景帝)宠信,号为“智囊”。
景帝即位,任内史,迁御史大夫。
吴楚七国叛乱时被杀。
“诛晁错,清君侧”
《汉书·艺文志》著录晁错文31篇,今存比较完整的有8篇。
其中《贤良文学对策》、《守边劝农疏》、《言兵事疏》、《论贵粟疏》最有名。
其文论事说理,切中要害,分析利弊,具体透彻。
唯文采略逊于贾谊。
《论贵粟疏》是作者上给汉文帝的奏疏,上承贾谊《论积贮疏》而发,进一步提出务农贵粟的主张。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瘠(zì胔)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xia散布、消散)。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云:“晁贾性行,其初盖颇同,一从伏生传《尚书》,一从张苍受《左氏》。错请削诸侯地,且更定法令;谊亦欲改正朔,易服色;又同被功臣贵幸所谮毁。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司马迁亦云:‘贾生晁错明申商。’惟谊尤有文采,而沉实则
稍逊,如其《治安策》,《过秦论》,与晁错之《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然以二人之论匈奴者相较,则可见贾生之言,乃颇疏阔,不能与晁错之深识为伦比矣。”
西汉鸿文:
语出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是鲁迅对贾谊的《治安策》、《过秦论》和晁错的《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等文章的评价。两人欲行变革,却被功臣贵幸所谮毁,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影响深远。
“西汉鸿文”的特征:
1、汉代初年,学尚黄老,文化思想相对自由。兼之战国纵横余风犹存,作者为文,较能畅所欲言,文章具有铺陈壮大的风格。
2、文人从政机遇尚多,社会生活相对稳定,有条件对历史、现实、人事作深入具体的思考和研究。这时的文章,
大抵论证充分、逻辑严密,少有
策士之辞的浮靡与诡辩。文章的结构和语言,也趋于详密和严整。
3、汉初文人抚今追昔,对当代社会的统一与安定倍感珍惜。他们以强烈的历史感与现实感总结前朝的兴亡教训,为统治阶级提供经验与借鉴,史论而兼政论、冷静客观而兼热情洋溢,是这一时期文章的又一特点。
四、邹阳
文景时人,曾为吴王和梁孝王门客。著有《上吴王书》、《狱中上梁王书》。
第三节枚乘
枚乘(?——前140)
字叔,淮阴人。
汉初重要的辞赋家。
初为吴王刘濞郎中,劝阻吴王谋反无效,改作梁孝王门客。
“梁客皆善辞赋,乘尤高”。
梁孝王死,归故里。
武帝即位,以“安车蒲轮”征聘他,因年老病死途中。
《汉书·艺文志》著录乘赋九篇。
《梁王菟园赋》、《忘忧馆柳赋》均为前人所称道。
然以《七发》最为著名:
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曰:“伏闻太子玉体不安,亦少间乎?”太子曰:“惫!谨谢客。”客因称曰:“今时天下安宁,四宇和平,太子方富于年。意者(料想是)久耽安乐,日夜无极,邪
气袭逆,中若结轖(“塞”的假借字)。纷屯澹淡(昏乱、摇荡),嘘唏烦酲(病酒),惕惕怵怵(心神不宁、忧烦惊惧),卧不得瞑(眠)。虚中重听,恶闻人声,精神越渫(xia)(越渫:涣散),百病咸生。聪(听觉)明(视觉)眩曜(yào)(眩曜:惑乱),悦怒不平。久执不废,大命乃倾。太子岂有是
乎?”太子曰:“谨谢客。赖君之力,时时有之,然未至于是也。”客曰:“今夫贵人之子,必宫居而闺处,内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交结朋友)无所。饮食则温淳甘膬(同“脆”),脭(ch?ng肥肉)醲(n?ng厚酒)肥厚;衣裳则杂遝(tà杂遝:众多)曼(轻细)煖(暖),燂(xún火热)烁(热)热暑。
虽有金石之坚,犹将销铄而挺(解)解也,况其在筋骨之间乎哉?故曰: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者,伤血脉之和(调和)。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蹷(ju?蹶)痿(蹷痿:麻痹瘫痪不能行走的病症)之机(机兆);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今太
子肤色靡曼(柔弱),四支委随(不能屈伸),筋骨挺解,血脉淫濯(脉大而软),手足堕(懈怠)窳(yǔ弱);越女侍前,齐姬奉后;往来游醼(通“宴”),纵恣于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止),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如
太子之病者,独宜世之君子,博见强识,承间语事,变度(du?考虑)易意,常无离侧,以为羽翼。淹沉(耽溺)之乐,浩唐(通“浩荡”,放荡貌)之心,遁佚(放纵过度)之志,其奚由(何从)至哉!”
太子曰:“诺。病已,请事此言。”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
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之,不欲闻之乎?”
太子曰:“仆愿闻之。”
以下分述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观涛六事,一步步启发太子。
最后是“论道”,用“要言妙道”进一步启发太子:
客曰:“将为太子奏方术(道术)之士有资(资望)略(智略)者,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渊)、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筹(筹划)之,万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
于是太子据(扶)几而起,曰:“涣乎(清醒貌)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niǎn)然(涊然:汗出貌)汗出,霍然(疾速貌)病已。
一、“七发”的意义
“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文心雕龙·杂文》)
李善注云:“《七发》者,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见《文选》卷三十四)
后一种解释比较符合作者原意。
这是劝戒膏梁子弟的一篇成功之作。
二、《七发》的艺术成就
1、《七发》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对先秦文学多有借鉴。
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机;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
——《吕氏春秋·本生》
在体制与描写手法上都受到过楚辞的影响,《离骚》的宏大体制及其中的问答形式、《招魂》帝与巫阳的问对,以及《招魂》和《大招》的铺排描写手法,还有纵横家说辞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区别在于,《招魂》和《大招》的铺排对象都是作为正面事物出现,以此诱导游魂的回归;而《七发》则把上述铺排对象作为否定性因素加以处理,是对贵族公子养尊处优生活方式的批判。
2、《七发》在艺术上的特色是铺张。
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
——《文心雕龙·杂文》
3、《七发》的出现,对汉赋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和影响。
第一,《七发》是在一个虚构的故事框架中以问答体展开的。
第二,《七发》脱离了楚辞的抒情特征,转化为以铺陈写物为中心的高度散文化的文体。
第三,《七发》所铺陈的内容,从多方面开拓了文学的题材,这些题材在后来的赋作中得到进一步发挥。
第四,《七发》已经出现了道德主题与审美主题的矛盾,也就是“劝百讽一”的现象,这也成为后来汉赋的基本特征。
4、《七发》既奠定了典型的汉代大赋的基础,又是辞赋中特殊的一支——“七”体的开创之作。
如傅毅《七激》、崔骃《七依》、张衡《七辨》、崔瑗《七厉》、曹植《七启》、王粲《七释》、左思《七讽》等。以至《文选》别立“七”体。
枚乘的散文:
《谏吴王书》、《重谏吴王书》。
第四节司马相如及其他作者
司马相如(?——前118)
字长卿,蜀郡成都人。
青少年时期,好读书,又学击剑。
初入仕途,“以赀为郎”,任“武骑常侍”,时随从天子(景帝)狩猎。
以有病为由,客游梁,成为梁园文学群体中的一员,作《子虚赋》。
梁孝王卒,梁园宾客解体,相如归蜀。与临邛富家女卓文君结为伉俪。
武帝偶读《子虚赋》,称赏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
恰好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于侧,遂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武帝十分惊喜,遂召相如。
相如见到武帝后,称《子虚赋》乃叙诸侯之事,不足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于是作《上林赋》。
武帝大悦,以相如为郎。
撰《谕巴蜀檄》以安抚巴蜀百姓。
见秦二世陵,作《哀秦二世赋》。
武帝好神仙,遂撰成《大人赋》。
《长门赋》为历代宫怨作品之祖。
还有《美人赋》、《难蜀父老》。
相如口吃而善著书,未尝肯与公卿交游。患消渴疾,常称疾避事。
晚年以病免官,居茂陵。武帝元狩五年(前118),终以消渴疾辞世。
相如居茂陵,亦时时著书,辄为人索去。
病逝后,朝廷遣人往取其所著书,仅有《封禅文》一篇奏上。
《子虚赋》、《上林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也是汉赋中具有开拓意义和典范作用的成果。
这两篇作品不作于一时。
《子虚赋》作于相如为梁孝王宾客时;《上林赋》作于武帝召见之际,前后相去十年。
两赋内容连属,构思一贯,结体谨严,实为一篇完整作品。
作品虚构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人,通过他们讲述天子、诸侯苑囿之大、田猎之盛。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讽谏。
楚使子虚使于齐,王悉发车骑,与使者出畋。畋罢,子虚过(过访)奼(诧,夸耀)乌有先生,亡是公存焉。坐定,乌有先生问曰:“今日畋乐乎?”
子虚曰:“乐。”“获多乎?”曰:“少”。“然则何乐?”对曰:“仆乐齐王之欲夸仆以车骑之众,而仆对以云梦之事也。”曰:“可得闻乎?”子虚曰:“可。王车架千乘,选徒万骑,畋于海滨……射中获多,矜而自功,顾谓仆曰:‘楚亦有平原广泽游猎之地饶乐若此者乎?楚王之猎,孰与寡人乎?’仆下车对曰:‘臣,楚国之鄙人也。幸得宿(值宿)卫(守卫)十有余年,时从出游,游于后园,览于有无,然犹未能遍睹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泽乎?’齐王曰:‘虽然,略以子之所闻见而言之。’仆对曰:‘唯唯。’”“‘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臣窃观之,齐殆不如。’于是齐王无以应仆也。”乌有先生曰:“是何言之过也!足下不远千里,来贶(kuàng赐)齐国;王悉发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与使者出畋,乃欲戮力致获,以娱左右,何名为夸哉?问楚地之有无者,愿闻大国之风(美好的风俗)烈(光辉的事业),先生之余论也。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然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先生又见(受到)客(宾客的礼遇),是以王辞不复,何为无以应哉?”(《子虚赋》)亡是公听(yín)然而笑,曰:“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也。夫使诸侯纳贡者,非为财币,所以述职也;封疆画界者,非为守御,所以禁淫(淫放,放纵侵犯别国)也。今齐列为东藩,而外私肃慎,捐(弃、离开)国逾限,越海而田。其于义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
“且夫齐楚之事,又乌足道乎!君未睹夫巨丽也(耶)?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于是乎游戏懈怠,置酒乎颢天之台,张乐乎膠(胶)葛(膠葛:寥廓空旷)之
宇,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虡(jù古代悬挂钟或磬的木架子),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
“于是酒中乐酣,天子芒然(茫然)而思,似若有亡(亡失),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览听余闲,无事弃日,顺天道以杀伐,时休息以于此,恐后世靡丽,遂往而不返,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
“从此观之,齐楚之事,岂不哀哉!地方不过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本不得垦辟而人无所食也,夫以诸侯之细(国小),而乐万乘之所侈,仆恐百姓被其尤也。于是二子愀(qiǎo脸色改变)然改容,超(通“怊”,怊chāo :悲、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讳,乃今日见教,谨受命矣。”(《上林赋》)
一、《天子游猎赋》的主题
《天子游猎赋》前后两部分主题是统一的,即反对奢侈,崇尚节俭,抑诸侯而尊
天子,维护汉帝国的统一。其间又有对人民生产、生活的关心,及对天子功德、帝国昌盛气象与风貌的热情歌颂。
二、《天子游猎赋》在汉赋史上的地位。
1、确立了汉大赋虚构人物、设为问答、铺张扬厉的体制;
2、奠定了大赋讽劝兼杂、“劝百讽一”的主题模式;
3、其体制成为后世赋家学习模仿的典范。
汉大赋:
汉大赋是汉赋的典型形式,形式上篇幅较长,多采用主客问答形式,内容上以体物为主,以润色鸿业为目的,兼有讽喻劝谏,艺术上采用铺张扬厉的手法和博富绚丽的辞藻,具有富丽堂皇的风格。以枚乘《七发》为形成标志,以司马相如《子虚》、《上林》最为典型。
汉大赋的特点:
1、篇幅较长,结构宏大,一般都在千字以上。
2、善于用铺陈、夸张的手法,富丽的辞藻。
3、侧重铺写宫苑、京都、宫殿、山川等壮丽事物,帝王的政治、军事、祭祀等重大活动,以及帝王贵族声色犬马、畋猎驰逐等生活。
4、主旨则既美且刺。其效果往往是“劝百讽一”。
5、多采用主客问答式,赋文一般由序、正文(主客彼此夸耀)、结尾(往往以一方向另一方诚服作结)。序和结尾一般用散文,正文以韵文为主。
“劝百讽一”:
语出西汉末扬雄的《法言》,是扬雄对汉大赋的批评。“劝”是鼓励的意思,“讽”即讽谏。其意是说赋中鼓励的成分过多,
淹没了篇末的讽谏主旨,本末倒置,结果欲讽反劝,适得其反,助长了帝王的奢侈心理。
枚皋
汉代文坛成果最多的作家。
枚皋是枚乘的庶子。史称其作品可读者百二十篇,此外尚有数十篇。他的作品不以讽喻谏说为宗旨,表现出有别
于传统的审美情趣和文学观。然其作品多匆促而就,缺少锤炼,故后世罕有流传。
东方朔
武帝周围文学侍从中较突出者。
为人滑稽多智,时时进谏,然多以诙谐话语论事,指意放荡,故终不见重用。
作《答客难》以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另有《非有先生论》、《七谏》。
后世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张衡《应间》等,皆模仿《答客难》。
刘安《淮南子》
淮南王刘安招致门客编成,今存21篇。原名《淮南鸿烈》,“鸿”是广大之意,“烈”是光明之意。
以道家思想为主而杂以孔、墨、申、韩之说,是汉初黄老思想的继续。
多用历史、神话、传说、故事来说理,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
淮南小山《招隐士》。
第二章
古代诗歌总集——诗经
第一节《诗经》概述
一、《诗经》名称之由来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
《诗经》被称为“经”,始见于《庄子·天运》之所载:
《庄子·天运》云:“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
《庄子》所谓经,只是书籍之意。汉代提倡儒术,将据说经过孔子整理的书,都称为“经”,作为常法,尊为经典。于是《诗》与《书》、《礼》、《易》、《春秋》并称“五经”。
二、《诗经》的篇目
《诗经》共有305篇,另有6篇笙诗,有目无辞。
这6篇笙诗是小雅中的《南陔(gāi )》、《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
有人认为本来有词,在战国至秦之世亡佚了(郑玄《笺》据《毛诗序》说);有人认为本来就是有声无词,“《南陔》以下,今无以考其名篇之义,然曰‘笙’曰‘乐’曰‘奏’而不言歌,则有声而无词明矣。”(《诗集传》)较为通行的说法,笙诗是有声无词的笙曲。
三、《诗经》所反映的时代
主要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
《诗经》中的作品,其创作年代的上限,由于人们对于商颂的理解存在分歧,故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古文经学家:
商颂为商人所作。
今文经学家:
商颂为春秋时宋人所作。
但商颂在《诗经》中所占的比例很小,《诗经》仍主要是一部周诗集。
《诗经》中最早的诗篇应该是《幽风》之《东山》、《破斧》、《鸱枭》。
《东山》和《破斧》是周公东征时的作品。《诗序》说:“《东山》,周公东征也。周公东征,三年而归,劳归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也。”
又说:“《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恶四国焉。”周公东征是在周成王三年和四年,公元前1113年至公元前1112年。《鸱枭》作于成王四年,是诛杀管蔡后,周公写给成王的。
《诗经》中作品的下限为春秋中叶是肯定的。最晚的作品大多认为是《陈风·株林》,大约创作于公元前599年(鲁宣公十年)前。
《诗序》说:“《株林》,刺灵公也。淫于夏姬,驱骋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陈灵公的事情在《左传》宣公九年和十年有记载。
也有人认为是《曹风·下泉》。
(陆侃如、冯沅君认为《曹风·下泉》作于公元前510年之前。见其所著《中国诗史》)。
《诗经》最后编定成书,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
四、《诗经》产生的地域
《诗经》产生的地域,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以及湖北的北部一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