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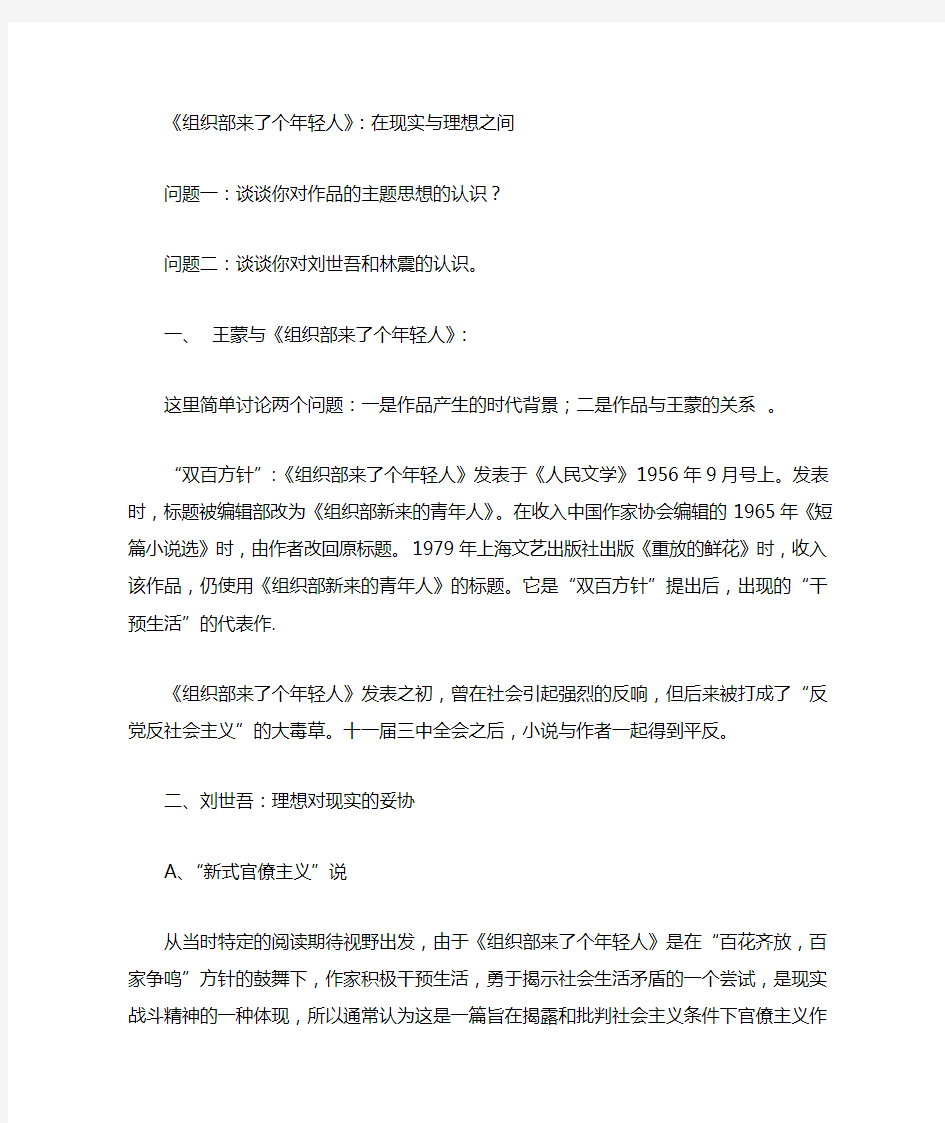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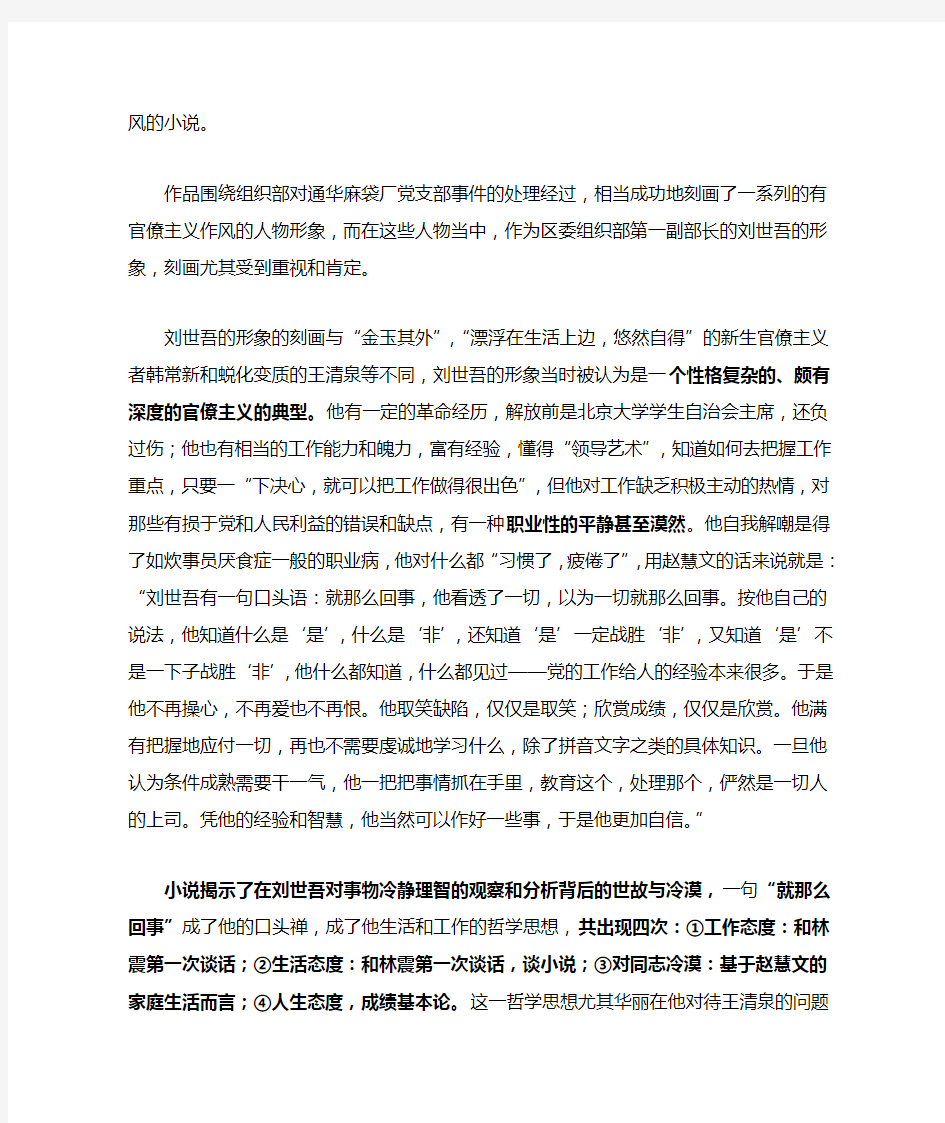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在现实与理想之间
问题一:谈谈你对作品的主题思想的认识?
问题二:谈谈你对刘世吾和林震的认识。
一、王蒙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这里简单讨论两个问题:一是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二是作品与王蒙的关系。
“双百方针”:《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于《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上。发表时,标题被编辑部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收入中国作家协会编辑的1965年《短篇小说选》时,由作者改回原标题。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重放的鲜花》时,收入该作品,仍使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标题。它是“双百方针”提出后,出现的“干预生活”的代表作.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之初,曾在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但后来被打
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小说与作者一起得到平反。
二、刘世吾:理想对现实的妥协
A、“新式官僚主义”说
从当时特定的阅读期待视野出发,由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作家积极干预生活,勇于揭示社会生活矛盾的一个尝试,是现实战斗精神的一种体现,所以通常认为这是一篇旨在揭露和批判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主义作风的小说。
作品围绕组织部对通华麻袋厂党支部事件的处理经过,相当成功地刻画了一系列的有官僚主义作风的人物形象,而在这些人物当中,作为区委组织部第一副部长的刘世吾的形象,刻画尤其受到重视和肯定。
刘世吾的形象的刻画与“金玉其外”,“漂浮在生活上边,悠然自得”的新生官僚主义者韩常新和蜕化变质的王清泉等不同,刘世吾的形象当时被认为是一个性格复杂的、颇有深度的官僚主义的典型。他有一定的革命经历,解放前是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还负过伤;他也有相当的工作能力和魄力,富有经验,懂得“领导艺术”,知道如何去把握工作重点,只要一“下决心,就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出色”,但他对工作缺乏积极主动的热情,对那些有损于党和人民利益的错误和缺点,有一种职业性的平静甚至漠然。他自我解嘲是得了如炊事员厌食症一般的职业病,他对什么都“习惯了,疲倦了”,用赵慧文的话来说就是:?刘世吾有一句口头语:就那么回事,他看透了一切,以为一切就那么回事。按他自己的说法,他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还知道‘是’一定战胜‘非’,又知道‘是’不是一下子战胜‘非’,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见过——党的工作给人的经验本来很多。于是他不再操心,不再爱也不再恨。他取笑缺陷,仅仅是
取笑;欣赏成绩,仅仅是欣赏。他满有把握地应付一切,再也不需要虔诚地学习什么,除了拼音文字之类的具体知识。一旦他认为条件成熟需要干一气,他一把把事情抓在手里,教育这个,处理那个,俨然是一切人的上司。凭他的经验和智慧,他当然可以作好一些事,于是他更加自信。?
小说揭示了在刘世吾对事物冷静理智的观察和分析背后的世故与冷漠,一句?就那么回事?成了他的口头禅,成了他生活和工作的哲学思想,共出现四次:①工作态度:和林震第一次谈话;②生活态度:和林震第一次谈话,谈小说;
③对同志冷漠:基于赵慧文的家庭生活而言;④人生态度,成绩基本论。这一哲学思想尤其华丽在他对待王清泉的问题上:当他一听到林震提起官僚主义者王清泉时,他立刻微笑着问首:“他是在下棋呢还是在打扑克?”林震对他如此了解王清泉感到惊奇,他便漫不经心地说:“他老兄什么时候干什么我都算得出来。”但他对王清泉的问题却觉得“就那么回事”,置若罔闻,不加过问。当韩常新汇报工作时,他听出了漏洞,突然指出:“上次你汇报的情况不是这样!”致使韩常新非常被动,不自然地笑着,但他觉得韩常新的不老实也不过“就那么回事”,也不深入追究。当他了解到韩常新所写的“麻袋厂发展工作简况”不真实时,他大笑起来,说:“老韩……这家伙……真高明……”从笑声里可以看出,他并认为韩常新的行为是对的,但他认为这也不过“就那么回事”,一笑置之。
这一方面反映了他的消极怠惰,另一方面渗透了他对现实生活的漠视。
作品塑造这个形象的深刻之处还在于揭露了刘世吾有一套似是而非的理论:如“领导艺术论”:“成绩基本论”:?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前进中的缺点,我们伟大的事业,正是由这些有缺点的组织和党员完成的?;“条件成熟论”、“职业病理论”等等。他的缺点是溶化在他的工作成绩里头的:?就象灰尘飘散在新鲜美好的空气里一样,能看见,能感觉到,但抓不住。?
B、理想对现实的妥协
然而,一旦跳出了那个特殊的历史语境,我们会发现,刘世吾这个人物形象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并不是“官僚主义者”这一概念可以概括的,即使是主人公林震本身,对刘世吾的态度和看法也始终都是复杂而矛盾的。如果说林震对韩、王两人的态度是明显的反感和对立,那么他对刘世吾的态度是十分复杂的,其中既有疑惑、质疑和批判,也包含了理解、同情甚至钦佩的成分,他的内心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体现在这里。
一方面,他对刘世吾的处世态度、工作作风抱有审视和批判的意识,但另一方面,刘世吾身上所具备的许多东西,如处事不惊的沉着、观察分析的冷静理智、传奇般的经历、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等等,都是林震并不反感甚至是钦佩的。甚至在对于韩、王这样的干部问题上,刘世吾和林震一样,在心里也很反感,相反对林震则认为“你这个干部好,比韩常新强”。但他又对林震的工作热情和主动精神,却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
小说中的所有人物中,除赵彗文外,林震与刘世吾之间有着很深入的思想和情感交流。在小说中,林震与刘世吾的对话主要有四次(),每一次出场,作者都没有把刘世吾这个人物作单一化处理,尤其是第四次在小饭馆的夜谈,使刘世吾的性格心理及其演变轨迹获得了较为完整和深入的体现。
作者反复强调的刘世吾对文学作品熟悉与喜好,正表明这个人物的内心深处仍拥有一块理想的田地,这种理想的激情也曾经使他冲动,而现在则被现实与理智牢牢地锁在文学想象的角落里了。这既使林震感到迷惑、惶恐和感伤,又引起他的警惕和质疑,他担心自己的理想和激情是否也会被现实所磨灭,他痛苦地探
问这种理想与激情是怎样变得淡漠的。
从很多方面看,刘世吾都是一个优秀的领导干部,并且曾经和林震一样是一个富有激情理想的共产党员,然而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看到了今天这样一个用现实与理智把理想的激情牢牢地锁在文学想象的角落里,对什么都“习惯了,疲倦了”,世故与冷漠的刘世吾呢?
这样一个刘世吾,同样的产生于理想和现实的距离之间。
林震对刘世吾的审视和批判,包含了作者的严肃思考;而对刘世吾的超越也是他走向成熟的开始。所以,刘世吾的形象并不是“官僚主义者”这一概念可以概括的。至少,从刘世吾这一形象可以看出,揭示现实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只是对《组织部来了个青年人》外在冲突意义上的概括,并不能完整地体现这篇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特性。
刘世吾的形象在作品中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一形象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对于文艺作品如何表现人民内部茅盾,揭露官僚主义这一严肃课题,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功。如果说苏联小说《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里的娜斯佳是林震理想中的人生偶像,那么在他具体生活境遇中,刘世吾象征了现实对理想的冲击,或者是理想对现实的妥协。林震与刘世吾的根本冲突在于:林震企图用理想去
改造现实,而刘世吾则用现实去否定理想。
三、林震——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展示其心路历程
(成长的小说,成长的挫折与痛苦)
在过去那种阅读和分析的视野里,相对于对刘世吾形象的重视和争议而言,对作为小说叙述人和主要人物的林震形象,虽然也有大致准确的把握,认为他是小说中与刘、韩等人物对立的中心人物,一个热情单纯,富有理想,朝气蓬勃,正在成长的青年共产党员的形象,但这一形象在小说叙述结构中的作用和与作品主题的关联则明显地存在被忽视的倾向。
当年对这一形象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说法:一说林震是“党的力量”;一说林震是个狂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
从小说的文本实际来看,《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虽然具有揭示官僚主义现象、“积极干预现实”的外部写真倾向,但它更是一篇从个人体验和感受的角度切入,通过个人的理想激情与现实环境的冲突,表现叙述人心路历程的成长小说。
主人公从一个小学教师的岗位,带着一种“节日的兴奋”来到组织部这个新的工作环境,结果却发现这里的情形与自己的想像有着很大的差距,一些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革命意志和工作热情的衰退使他愤怒、疑惑,他为自己无法融合于这一环境而惶恐、伤感。与对外部冲突的再现相比,作者更注重对叙述人心理内部冲突的表现;甚至可以说,对心理冲突事件的精彩呈现,才是这篇作品的艺术独特性所在;小说的主题和现实针对性也只有在对其内部视角的分析中获得更切实的理解。
主人公林震快乐、单纯、富于青春的朝气和理想的激情,他是怀着一种成长的渴望和焦虑来到组织部的,二十二岁的“生命史上好象还是白纸,没有功勋,没有创造,没有冒险,也没有爱情”,他奉娜斯佳(1956年,《中国青年》杂志开
展了对苏联小说《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的讨论(在此之前,《中国青年》上连载了
这部小说。)。拖拉机站站长是小官僚,娜斯嘉是总农艺师。苏联当时盛行歌功颂德、虚
报瞒报风,娜斯嘉亲眼目睹了那种官僚氛围,那种权和钱交易的腐败现象,她看不惯。当
上级领导来视察的时候,当拖拉机站站长、当那些吹牛拍马的人汇报工作的时候,娜斯嘉忽然站了起来,当着领导的面,她说:这些都是假的,让我告诉你真实的情况……《中国青年》当时编发了一个编者按,编者按中提倡娜斯嘉精神,即提倡说真话的精神、提倡干预生活。别说是那个时代,就是以现在的目光看,都是那么有预见性,都是那么地针砭时弊。)为人生偶像,在“社会主义高潮的推动”下,要“努力工作”,要“学这学那”,要“做这做那”,要“一日千里”。组织部是他走向成熟,实现人生理想的新的环境,而小说也正是以林震的心理体验为视角,在工作历练和爱情体验这两条线索上,通过麻袋厂事件的始末,展开对理想与现实之冲突的叙述。(作品的第一章,林震刚来组织部报到,就出现了两个人物,一个是?苍白而美丽的脸上,两只大眼睛闪着友善亲切的光亮?的赵慧文;一个便是常务副部长刘世吾,而刘世吾对他的第一次谈话,恰恰涉及了工作与爱情这两个话题。而这两个方面相互交织、矛盾和冲突,对初涉人世的林震来说又都带有?冒险?色彩。)然而在工作和爱情这两条互相交织的线索中,小说还是侧重于体现由于一些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革命意志和工作热情的衰退,而使他愤怒、疑惑,他为自己无法融合于这一环境而惶恐、伤感——爱情的线索是依附于工作这条主要的线索之上的。
50年代中期,新中国的生活刚刚展现它的魅力,周围弥漫着早春的气息,一切都充满生机。但作家却敏感地对此投出了怀疑的目光,他通过林震的内在视角,在两条冲突线的交织中表现出:就在这一片生机里,有一种可怕的惰性在蔓延,就在刘世吾那些据之有理的逻辑和成熟举动的背后,有某种不可原谅、不能妥协的东西,他对之不满甚至力图反抗。尽管对于林震而言,斗争的对象似乎无处不在,有王清泉式、韩常新式的在明处;也有刘世吾式的象泥鳅一样滑腻;斗争的过程中也不免要付出某种代价,但他偏偏以一种执拗的“幼稚”进行着力量悬殊的斗争,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至今还散发着青春激情的芬芳,也超出了对官僚主义揭露与批判的具体性,而体现出理想与激情的永恒魅力和对现实的审视批判意义。
可以说,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林震面临的困惑也就是我们面临的困惑,林震感到的痛苦也就是我们共同的痛苦,林震经过的心路的历程,正是最打动读者的地方之一。
四、青春时代的情感苦闷——关于林震与赵慧文
与赵慧文的交往是林震心理历程中的另外一条线索。
小说中有这么几个情节值得重视:
一是赵慧文和她当科长的丈夫的感情不好,生命中出现了一种“空白”;
二是赵慧文和林震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斗争、气质、性格、年龄等);
三是这个形象渗透着作者王蒙对生活对生活的认识、感受和理解。王蒙当年22岁,正处在林震的年龄,正经历着林震的苦闷、伤感和惆怅。
作者暗示了林震对赵慧文朦胧的爱情意识,即?两个人交往过程中的感情的轻微的困惑与迅速的自制?。在作品所呈现的外在冲突中,他们是相互理解的同志,从某种意义上说,赵慧文是比林震先到一步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而在林震的内心冲突中,他与赵慧文的情感涟漪也是一个重要的侧面,在林震对现实的质疑、惶惑、孤立无援之时,有一双忧郁而美丽的眼睛注视着他,两颗年轻的心来不及相互靠拢,就为几乎是预设的“警告”所阻隔,林震在内心矛盾中对这份情感的克制,是爱情需要对事业需要的退让,也是现实原则对内心欲求的胜
利,最后所作的理智选择同样体现了他的成长。
五、小说文本结构的隐含特征
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后,批评家的阐释已成定论,但当代读者的阅读经验却与之悖反,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作品虽然采用的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叙事笔法,但却具有两重结构、双重视角——显在的和潜在的。
显在结构:呈现的是青年人林震同区委组织部存在的官僚主义和干部思想老化现象的斗争。这是小说的外部结构,小说的各个环节都是围绕着林震的遭遇和命运这条展开的。
林震对刘世吾的审视和批判,包含了作者的严肃思考;而对刘世吾的超越也是他走向成熟的开始。至少,从刘世吾这一形象可以看出,揭示现实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只是对《组织部来了个青年人》外在冲突意义上的概括,并不能完整地体现这篇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特性。
潜在结构:隐含的是刘世吾对自己的革命热情衰退的不满以及林震内心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或者说是青年林震在理想与现实冲突下的心路历程,是连续的斗争史和连续的碰壁史。
与对外部冲突的再现相比,作者更注重对叙述人心理内部冲突的表现;甚至可以说,对心理冲突事件的精彩呈现,才是这篇作品的艺术独特性所在;小说的主题(表现人的成长过程中的痛苦)和现实针对性也只有在对其内部视角的分析中获得更切实的理解。
显在结构和隐含结构的互补互动构成了作品的隐含文本:林震实为过去时态的“少共”王蒙的象征,刘世吾则是现在时态中作家心灵冲突的投影,通过对自身成长链条上的两个环节的描述,流露出作家在现实中无法使两个自我调适合度的困惑和隐忧。
林震是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朝气蓬勃、满怀革命理想、单纯热情的年轻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基层的党务工作者,他满怀着对党的事业的无比崇敬和对火热生活的热切向往,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的。他直率、认真、执著,对腐败的斗争、对权力的不屈、对真理的坚持,使他一次次跃过迷惘和困惑,同与工人对立的麻袋厂厂长王清泉斗争,同推委麻木的直接领导——韩常新怒目相对,同“一切看透了”,“一切就那么回事”的组织部副部长刘世吾据理力争。他积极地向上级汇报、反映情况,努力想办法解决问题。但得到的却是嘲讽、警告和批评,使他进一步陷入惶惑和苦恼之中。面对同样有着激情和理想,不甘心在日常琐事中逐渐沉沦却又无从倾诉的赵慧文,他虽未表现出悲哀与失望,却逐渐摆脱了对新工作、新生活的美好幻想,开始了认真、理性的思考。后来,由于市委和报纸的介入,使麻袋厂问题得以解决。在总结会上,林震提出了应防微杜渐、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主张,却又一次受到责难。几经思考,他终于鼓起勇气向组织部部长倾诉自己的想法……。小说成功地展现了他由单纯、幼稚到逐步成熟的过程,显现出年轻一代的成长和对未来的热切希望。
刘世吾是一位生活经历丰富、工作能力很强的老干部,也是一位思想性格复杂的官僚主义者。作为区委组织部的第一副部长,他一方面具有很“强”的党性,经过艰苦的战争生活的考验和锻炼,而且社会经验丰富、工作能力很强,“一下
决心,就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出色。”另一方面在对待具体工作和问题时,却又显如此的惰性,他那闪烁其辞的话语和躲躲闪闪的作为,更多的是给人以“和稀泥”的感觉,甚至可以说,他就是组织机制失灵的始作俑者。在处理问题时,他往往把组织处理轻描淡写地解释为“经常教育”;面对具体问题,又强调“条件成熟”说——总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为借口——搪塞及时解决问题的职责,既缺少主动性,又缺乏激情,因此,他沮丧地认为:“我们创造了新生活,结果,生活倒不能激动我们。”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就那么回事”。于是,他可以“苦口婆心”地忽视林震的敏感,也能够“慈悲为怀”地宽容韩常新的简单和粗糙,最后也就必然“铮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容忍”了王清泉的堕落。小说没有把这个人物类型化,而是深入地挖掘了他的内心世界,展现了他麻木而痛苦的心灵——为了排解内心的郁闷,他偶尔回忆起往日的战斗生活,也会感慨无限;读到一本好小说,也会兴奋地评论一番;甚至一场小雨,也会令他想到许多许多……。尽管如此,他始终未能从暗淡的心态中自拔,麻袋厂问题的解决也没能使他真正觉醒。作品的深刻之处,还在于揭示了他的一整套似是而非的“理论”,诸如“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前进中的缺点。我们伟大的事业,正是有这些有缺点的组织和党员完成的”等等,进一步深了这一形象的典型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