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张志公语文教育思想简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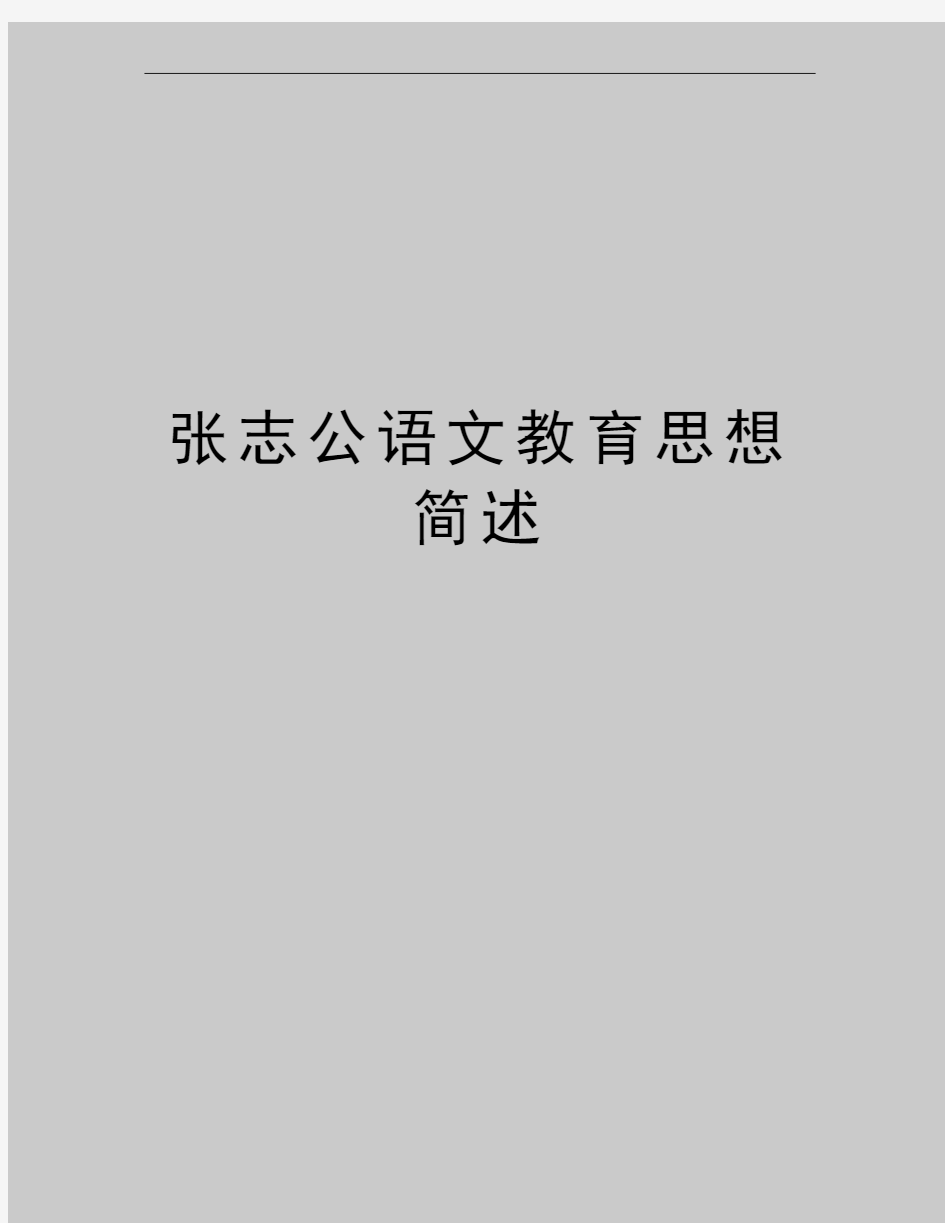

张志公语文教育思想
简述
传统与现代的理想对接
——张志公语文教育思想简述
一、张志公生平简介
张志公先生(1918—1997),1918年11月生于北京,祖籍河北省南皮县。1937年就读于中央大学外语系,攻读英语、法语和外国文学;1940年辍学,后转入金陵大学外语系;
1945年自金陵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
1946年起,自学俄语,并研究语言学和汉语;
在辍学和大学期间,先后在金陵中学、华西中学等中学任教;
1948年应聘到海南大学外语系任副教授,代理系主任;
在金陵大学、海南大学讲授英语、欧美名著选读和语言学概论等课程,并开始致力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研究,主要是汉语语法修辞;
1950年初,转赴香港华侨大学任教,讲授翻译学;
1950年10月,回到北京,在开明书店任编辑,分管外语、汉语和翻译书稿的编辑工作;
1951年负责编辑新创刊的《语文学习》月刊;
1953年,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张志公先生任编辑室主任,除继续主编《语文学习》外,仍主持语文、外文书籍的编辑工作;在此期间,开始被借用到语言所工作;
1954年,中国教育部确定中学语文科实行汉语和文学分科教学,委托吕叔湘先生和张志公先生主持编写汉语教材,为此,人民教育出版社设立了汉语编辑
室,张志公先生担任编辑室主任,《语文学习》杂志也改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张志公先生继续任主编;
此外,他还先后担任课程教材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会长、全国高等学校文字改革学会顾问、世界汉语教学研究会顾问、全国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委员等职。从此,张志公先生的事业基本上就定位在语文教材的编写和语文教育及其相关研究上,他探求面很广,设计和语言相关的诸多领域;
1997年6月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
张志公先生是一个学外语出身的人,但是他的主要建树不在外语教育和研究上,竟成为当代中国汉语语言学研究和语文教育研究的核心人物,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他的外语和语言学、汉语研究的背景,尤其是对中国传统语文教育的研究,使他具备了一般语文教育学者不具备的素养和眼光,他的语言学和汉语知识,使他对传统语文教育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而这种理解为他对现代语文教育进行的思考提供了参照系,他的很多语文教育著述,都有他对传统语文教育认识的影子,甚至直接渗透到了他对现代语文教育发展思路的设计和勾画中。他的研究,昭示了一个道理,不懂得传统语文教育,就不懂得当今的语文教育,不了解传统语文教育,就没有资格研究当今的语文教育。一位专家这样评述张志公的研究优势:一个学者除了先天的概念、逻辑思维的优势外,还需要具备三个方面的素养:一是对该领域基本学术资源的掌握;而是相关学术领域的学养和视野;三是基本的学术思维的能力和长期的学术写作的经验积累。而张志公先生这三个方面的素养无疑都在一般水准之上,他对传统语文教育所做的第一手的梳理,使之掌握的学科的历史资源比谁都多;在
相关学术领域的学养和视野方面也很突出,他的外国文学、外语教育和语言学、古今汉语知识,也具备了同时代人所不具备的优势;他的大量的、多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丰富多样的教学、科研阅历,也是很少有人可以企及的。因此,他的脱颖而出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二、张志公先生的主要学术研究领域及思想评介
(一)语言学研究
张志公是我国当代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他在汉语语法学、语汇学、修辞学和辞章学的研究中卓有建树。他主张汉语语法研究应该从汉语言的实际出发,摆脱印欧语语法框架的束缚,建立一个具有汉语特点的语法体系,并为此进行了创造性的实践。他紧紧抓住汉语作为“非形态”语言的特性,不断地提出发人思索的新问题、新看法。他先后两次主持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制订,为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的建立和更新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几十年的潜心研究,为的是在语言学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和实际的语言应用之间找到一个中介环节,使语言学的基础理论与知识能够付之于应用,使培养提高听说读写能力的语文教学能够得到语言理论的指导。这一新型学科的建构,对语言理论与语文教学的研究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推荐阅读:《汉语语法常识》《语法学习讲话》等专著,主编《现代汉语》教科书。
(二)语文教育研究
20世纪60年代,代表了语文学者的良知,填补了语文教育史研究的空白,80年代后引领语文教育的主流,在语文教育的科学化、语言学的实用化方面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1.关于传统语文教育的研究
一个学科,没有学科史,没有对学科史的建构,就不是一个成熟的学科。不论这个学科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历多长,只要它的过程、规律、方法、经验,它的思想范式和思维特征未经梳理,未经过时间的沉淀和理性的思辨,它都不具备作为一门现代科学的条件。学科史学,是学科从业者的思想资源库,是该学科的学者的精神家园。有了学科史学,学者的工作才有了积累和繁衍的处所,学者才有了归属感。学者要是没有学科史的背景,他的研究便是无“根”的研究,他的思考是漂浮不定的,他的思想是浅薄无知的,他的学问是没有皈依的。
语文学科已经有了三千多年的历史,张志公先生曾谈到,此前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只有中华书局收集并展览过五六十种童蒙读物,胡怀琛曾经写过一本《蒙书考》,开列了大约一百种所见所知的蒙书,辑录了几十条有关的资料:这些,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不过收集考察的范围都还不大,分析研究更付阙如。因此,张志公先生堪称对其作系统考察研究的第一人。
因此,我们不能不说张志公是有眼光的,他认为要提高语文教育工作有三件事需要做,其中之一就是对传统语文教育的研究:“首要的是研究我们的教育方针,研究社会主义建设所要求于语文教育的任务,研究我国语言文字的特点,研究我国当前青少年和儿童的语文状况,研究他们语言文字能力成长发展的规律,总结解放以来和解放前革命根据地的语文教育经验,总之是研究当前与语文教育有关的种种实际。与此同时,也还需要补作废科举兴新学以后,尤其是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就应该做而没有做,或者做得不够、不好的两项工作。一方面是研究我国语文教育的传统,看看其中哪些做法是坏的,错误
的,哪些是虽然不坏但已过时的,哪些是仍有现实意义的。……——对于传统的经验,过去几十年没有研究过,只是全盘地加以否定。……再一方面是研究外国的经验,包括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乃至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看看其中哪些是不见得对头的,哪些是虽然好而不适合我们的情况和需要的,哪些是于我们有用的。——对于外国的作法,过去几十年中多数时候是生搬硬套,认真的分析研究,做得也很少。这几方面的研究工作,都是相当艰巨的,然而都是必要的。”
张志公认为:“长期封建社会中形成的传统,肯定会有封建主义的坏东西,但是也绝不可能一点可取的经验都没有。一个关心今天的语言教育的人,不应当对这个深深影响着今天语言教育的体系——传统语文教育漠然置之,不加研究。”
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不论是提出要研究传统语文教育的经验,批评“全盘否定”的做法,还是对我们过去学习外国提出“生搬硬套”的批评,都是要担极大的政治风险的。而他却敢于直言不讳,可见其对学术的真诚。
传统语文教育资料纷繁,从哪里入手是个问题,张志公的研究选择了从教材入手。他认为研究历史上的语文教育,求之于教材往往比求之于史传记载的章程、条例更可靠可信一些,教材是实际使用的,而其余则往往是作出来的文章,说得头头是道,但与实际不见得相符……古今中外,语文教材对社会的发展变化最为敏感。它反映产生它的社会背景,包括文化传统、风土习俗等等,反应当时社会主导的思想意识,以及教育观点、教育政策,可以说语文教材是语文教育、思想教育、知识教育的综合性教育读物。所以研究教材的意义很大,收获会是多方面的。
张志公研究传统语文教育,就是通过对历代大量有代表性的教材及其教法的梳理分析进行的,整个研究过程前后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主要是从传统语文教育的做法中探求经验。他清晰地勾勒出了传统语文教育的三个阶段、四个步骤。第一阶段(第一、二年)是启蒙教育,分为两步:第一步是集中识字(二千个左右)。也可以说是初期的识字教育和写字训练,很突出的做法就是在儿童入学前后用比较短的一段时间(一年上下)集中地教儿童认识一批字——两千个左右;第二步是进一步识字教育,兼顾初步的知识教育。这一步强调识字教育与思想教育、知识教育相结合,在集中识字和开展认真的读写训练之间加上一个过渡性的阶段——继续进行识字教育,巩固前阶段所识的字,进一步再多识些字,比如说识到三千多个,与此同时,结合着多进行些思想教育,也进行些知识教育。第二阶段(第三年)即第三步为读写的基础训练。这个阶段一般的做法是:开始教学生读《四书》《五经》;配合读经,教学生阅读简短的散文故事和浅易的诗歌,教学生学对对子(属对),有的还交给学生一点极浅近的文字、音韵等语言文字的基础知识。第三阶段即第四步是进一步的阅读训练和作文训练。阅读训练和作文训练是这个阶段中语文教育密切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张志公所分的三阶段,大约涵盖了类似现今的基础教育阶段。但是传统语文教育由于教学内容较为单纯,不像“新学”(现今)开始后学得那么庞杂,所以,可以在较短的学习时间内取得较高的学习效率。大家工人,经历过“旧学”的,如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很多大家,国学、语文功底都比较好,他们在文学艺术领域达到的高度,是现今的许多作家无法企及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