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宣传构成欺诈之认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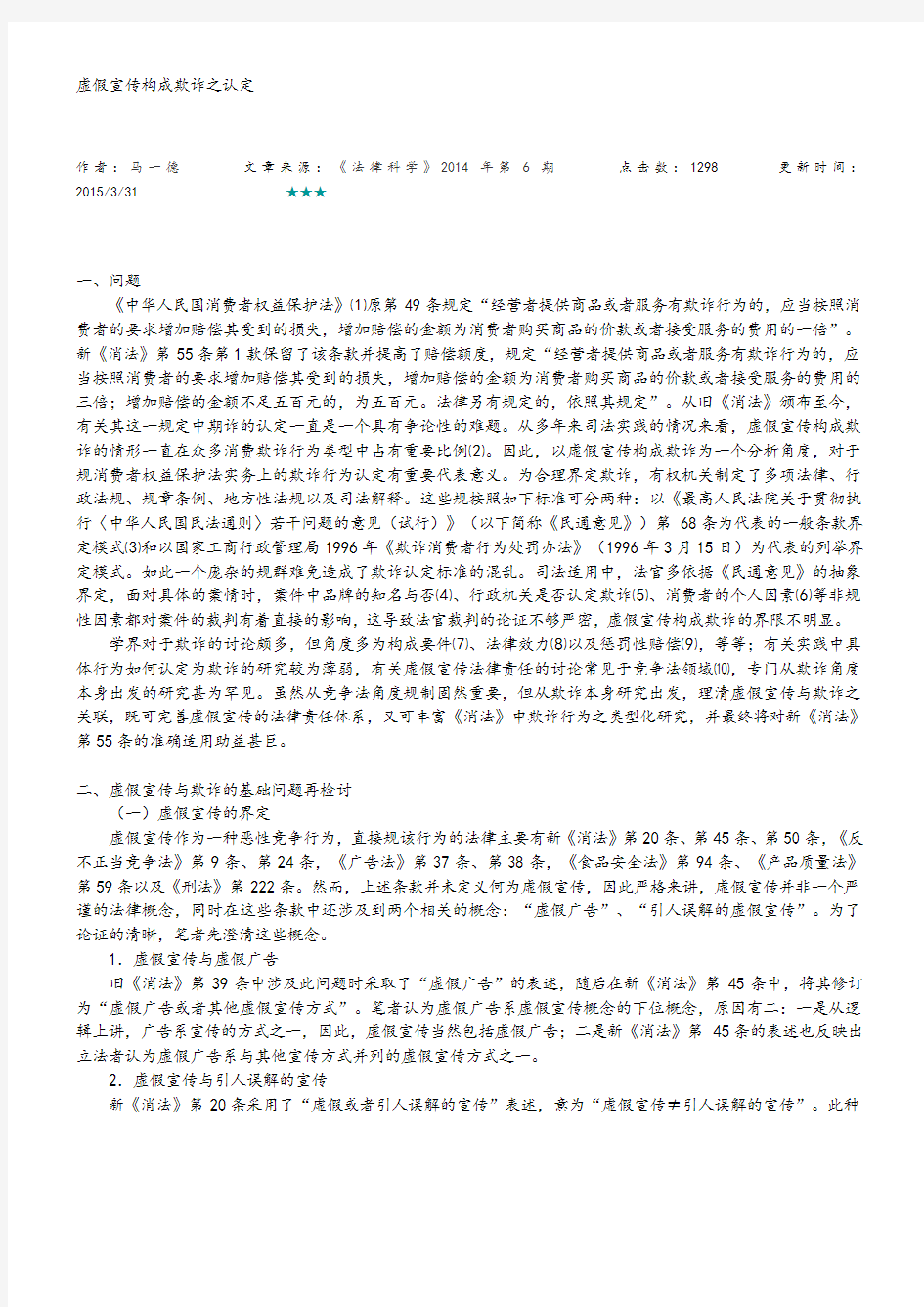

虚假宣传构成欺诈之认定
作者:马一德文章来源:《法律科学》2014年第6期点击数:1298 更新时间:2015/3/31 ★★★
一、问题
《中华人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⑴原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新《消法》第55条第1款保留了该条款并提高了赔偿额度,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从旧《消法》颁布至今,有关其这一规定中期诈的认定一直是一个具有争论性的难题。从多年来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虚假宣传构成欺诈的情形一直在众多消费欺诈行为类型中占有重要比例⑵。因此,以虚假宣传构成欺诈为一个分析角度,对于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务上的欺诈行为认定有重要代表意义。为合理界定欺诈,有权机关制定了多项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条例、地方性法规以及司法解释。这些规按照如下标准可分两种: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68条为代表的一般条款界定模式⑶和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1996年3月15日)为代表的列举界定模式。如此一个庞杂的规群难免造成了欺诈认定标准的混乱。司法适用中,法官多依据《民通意见》的抽象界定,面对具体的案情时,案件中品牌的知名与否⑷、行政机关是否认定欺诈⑸、消费者的个人因素⑹等非规性因素都对案件的裁判有着直接的影响,这导致法官裁判的论证不够严密,虚假宣传构成欺诈的界限不明显。
学界对于欺诈的讨论颇多,但角度多为构成要件⑺、法律效力⑻以及惩罚性赔偿⑼,等等;有关实践中具体行为如何认定为欺诈的研究较为薄弱,有关虚假宣传法律责任的讨论常见于竞争法领域⑽,专门从欺诈角度本身出发的研究甚为罕见。虽然从竞争法角度规制固然重要,但从欺诈本身研究出发,理清虚假宣传与欺诈之关联,既可完善虚假宣传的法律责任体系,又可丰富《消法》中欺诈行为之类型化研究,并最终将对新《消法》第55条的准确适用助益甚巨。
二、虚假宣传与欺诈的基础问题再检讨
(一)虚假宣传的界定
虚假宣传作为一种恶性竞争行为,直接规该行为的法律主要有新《消法》第20条、第45条、第50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第24条,《广告法》第37条、第38条,《食品安全法》第94条、《产品质量法》第59条以及《刑法》第222条。然而,上述条款并未定义何为虚假宣传,因此严格来讲,虚假宣传并非一个严谨的法律概念,同时在这些条款中还涉及到两个相关的概念:“虚假广告”、“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为了论证的清晰,笔者先澄清这些概念。
1.虚假宣传与虚假广告
旧《消法》第39条中涉及此问题时采取了“虚假广告”的表述,随后在新《消法》第45条中,将其修订为“虚假广告或者其他虚假宣传方式”。笔者认为虚假广告系虚假宣传概念的下位概念,原因有二:一是从逻辑上讲,广告系宣传的方式之一,因此,虚假宣传当然包括虚假广告;二是新《消法》第45条的表述也反映出立法者认为虚假广告系与其他宣传方式并列的虚假宣传方式之一。
2.虚假宣传与引人误解的宣传
新《消法》第20条采用了“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表述,意为“虚假宣传≠引人误解的宣传”。此种
表达方式与我国地区1992年“公平交易法”第21条的表述相同,该条规定:“事业不得在商品或其广告上……为虚伪不实或引入错误之表示或表征。”我国地区学者黄茂荣也将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他认为广告的虚伪不实判定应“先以其广告表示之容、从字义论与事实是否相符,然后再参酌其附随因素,寻求表意人已客观表达之真意”,而引入错误则系广告“是否具有使人陷入错误的作用”。[1](p422)然而,在我国的法律语境中,这两个概念区分并不明确,往往进行混用。体现如下:(1)法条之间常混用这两个概念。在前述规虚假宣传的规定中,旧《消法》第19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采用了“引人误解”的说法,而旧《消法》第39条、《产品质量法》第59条、《广告法》第37条、第38条则采用了“虚假”的说法,法条在规该行为时并未严格区分,而采取了混用的模糊态度。(2)司法实践中亦混用这对概念。以“黄志宏诉奇瑞汽车公司案”⑾为例,判决书中“被告的宣传行为仅系违反了《中华人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作为经营者禁止虚假宣传的禁止性规定”采取了“虚假”的表述,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中则为“引人误解”,因此,司法裁判者在适用时并未突出两者的区别。
究其原因,“引人误解”与“虚假”之间虽然方式不同,但两者的本质特征可总结为:均系宣传呈现的容不实,意图导致信息接受者产生错误认识,两者各为不实宣传的一种。笔者下文中讨论虚假宣传也均从这个意义出发,严格来讲,使用不实宣传可能更为贴切,但由于我国法律实践中已广泛使用虚假宣传的说法,笔者将沿用之。
(二)虚假宣传的民事责任
《消法》和《广告法》均规定了消费者有权以经营者发布“虚假广告”,要求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根据相关案例,消费者依据《广告法》第38条追究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发布者责任的,按照消费者实际损失进行赔偿。《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了经营者之间的民事赔偿责任,只有被侵害的经营者才有权以该法起诉。如消费者依据《消法》追究经营者责任,通常会依据新《消法》第45条追究,或通过新《消法》第55条要求认定经营者存在“欺诈消费者”行为,从而承担加倍赔偿责任。
1.根据新《消法》第45条规定:“消费者因经营者利用虚假广告或者其他虚假宣传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广告的经营者不得提供经营者的真实名称、地址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未对具体责任容进行明确。
2.根据新《消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这便将虚假宣传行为作为欺诈予以规。同时,《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第3条第9项规定“利用广播、电视、电影、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对商品作虚假宣传的”,认为“虚假宣传二欺诈”,但这种做法显然不符合传统欺诈要件的要求,过分降低了欺诈的认定标准,那么,符合什么程度的虚假宣传可认定为欺诈,新《消法》第55条中欺诈的认定标准又是什么?
(三)欺诈认定现行标准之再检讨
学界围绕欺诈的认定标准提出了“四要件说”、“三要件说”和“二要件说”,其中,作为传统的欺诈构成要件学说的“四要件说”学者认为欺诈的构成要件有:欺诈故意、欺诈行为、被欺诈方的错误认识与欺诈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被欺诈方因错误而做出意思表示⑿,而针对“四要件说”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其一,玉荣等学者认为民法中欺诈的四要件说存在问题,将欺诈与受欺诈行为混为一谈,进而提出欺诈的构成要件中不应包含“被欺诈方因错误而做出意思表示”要件⒀;其二,一些学者认为《消法》中的欺诈概念不同于《民法通则》,因此,为了更有效地保护消费者权益,其构成要件应重新界定,如取消故意要件或错误认识要件,进而形成了消法欺诈的“三要件说”⒁和“两要件说”⒂。笔者认为,新《消法》中第55条的欺诈构成应采“四要件说”,理由如下:
1.《民通意见》第68条认为“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确立了欺诈四要件的权威解释。同时,《消法》调整的是“处于特定身份和特定社会围的民事主体”,[2]新《消法》第55条所调整的是一个合同欺诈问题,[3]因此自然适用民法之一般规定,因此,从司法裁判的原理来讲,其应遵守的是《民通意见》的“四要件说”。
2.法律适用的目的并非是一味地保护一方的利益而忽视另一方的利益。如三要件说学者所言,为保护消费
者利益,应将故意要件排除,进而过失亦可构成欺诈,这在实际上不合理地加重了经营者的负担。从新《消法》第55条的条文来看,其保护消费者的措施在于经营者实施了欺诈行为后的结果加重,而并非将欺诈行为的认定标准降低。因此,欺诈的认定仍应坚持四要件说。
(四)虚假宣传之欺诈认定仍然是司法难题
从前述可知,欺诈的认定应逐步考察四个方面要件,因此,虚假宣传不能直接认定为欺诈,《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第3条第9项中类型化的尝试虽然值得肯定,但其未严格遵守上位法中确立的欺诈要件的做法并不妥当,导致了其原有意图的落空。然而仔细审视司法裁判中更常被引用的《民通意见》第68条,该条确立的仅是一个抽象的指引,并未回答在司法实践中欺诈包含哪些行为类型,什么程度的行为可认定为欺诈。这种抽象性的指引带来的是司法认定欺诈的无序,笔者试举两例说明:
在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年裁判的案件中,“正军诉易初莲花公司案”⒃和“极品羊肉卷案”⒄案情相似,均系商家宣传语采用了“极品”这样的绝对化用语,此行为违反《广告法》,前案中该行为已被行政机关认定为虚假宣传并予以处罚,而法官认为该行为仅系虚假宣传,并无欺诈故意,因此不认定为欺诈,而后办案法官认为该“极品”用语的虚假宣传误导了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应认定为欺诈。在确定性指引缺位的情形下,法官“自由裁量”的围过大,因此必须以规化的方式理清欺诈认定时的考虑因素,才能使司法裁判的可预测性更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有认真分析案例,才能提炼出司法裁判中虚假宣传认定欺诈的难点和解决之道。
三、将虚假宣传认定为欺诈的困难所在
(一)引人误解因素的评价
许多学者认为,欺诈行为的构成应有表意人的“错误意思表示”这一要件,即表意人因欺诈而陷于错误,并在此错误的指导下做出意思表示。非如此,虽有欺诈行为,亦不影响意思表示之效力。至于该错误“系动机错误或容错误,并无分别”。[4](p314)但是,这种错误的意思表示判断采主观标准还是客观标准,即是以案件当事人的主观意思为据,还是以普通消费者应当具有的正常认识为准,笔者通过几个案例予以说明。
1.明显夸情形:消费者最低限度常识的共识
对于一些常见的消费物品,法院明显倾向于采取“客观标准”,认为应以普通消费者的正常认知程度为准。在党参蜂蜜案中,被告销售牙膏时赠送的党参蜂蜜包装上有益于补中、益气生津、胃冷、慢性胃炎、贫血者保健食用等宣传字样,原告在实际食用后并没有产生预期功效。法院在欺诈认定时采客观标准,认为此种宣传行为不足以令“正常认知能力的普通消费者”作出错误购买的意思表示⒅。在社饭案中⒆,法院更进一步地明确指出,在判断错误认识时应采“整个消费群体对该商品的综合评价”,因此并不认为其构成欺诈⒇。
2.特殊情形下消费者的谨慎义务
虚假宣传明显违背常识的情况不予认定欺诈的做法虽无成文规定,但却有迹可循。而在其后隐藏的,实际上是对于消费者和销售者之间地位的权衡。若依照市场上普通消费者所应有的认知来认定欺诈所造成的意思表示,那么在许多情况下,消费者就被要求在行为初始具有一般甚至是更高的谨慎义务。这一点随着笔者的观察这种倾向也愈来愈明显。
在“水货镜头案”(21)中,作为初级摄影爱好者的原告在购买系争镜头时对市场上同类商品做过一定程度的调查,在知道同类商品因包装不同存在巨大价格落差的情况下,于被告处低价购买全镜头2只。法院认为,原告在获知以上信息之后,以被告故意欺诈为由进行诉讼实难符合一般人之常理,此举系其主动之行为。被告虽有出售水货之举,但难以构成对原告之欺诈。同样,一些法院认为在一般交易习惯下,原告应主动了解信息而怠于作为的情形下,可酌情不予认定经营者的欺诈行为。在“奇瑞汽车案”(22)中,法院认为对于大件商品,即使经营者的宣传方式可能给消费者带来一定误解,但消费者在此类消费过程中,按照交易习惯均会仔细考量、认真比较,无误后最终做出决策,经营者的虚假宣传行为与消费者的必然购买后果之间被消费者本身负有的谨慎义务所阻断,在“拾财诉丹尼斯案”(23)中也可看出法院的此种倾向。
如永军所言:“欺诈必须使对方当事人产生合理的信赖。”[5](p398)“合理的信赖”的表述中折射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需要考虑被欺诈人产生错误的信赖过程中其自身的过失?换句话说,被欺诈人作为当事人,其个人因素对于欺诈认定有无影响?
(二)部分虚假宣传问题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商品开始出现功能集合化的特征,而到底哪种功能才是消费者真正需要的功能,可能很多消费者自己都不清楚。同时在市场中,某些产品的宣传更是模糊其本身应有的界限,如诸多食品宣传的药用保健功能,新出现的电子产品难以准确定位为手机或是平板电脑等,而这种宣传上的模糊和混淆会不会给消费者造成错误的认识,也是新出现的一个问题。此种情况给虚假宣传认定欺诈时带来的一个问题:面对复合信息,如何判断消费者的行为与欺诈行为的因果关系?
法院在这个问题上颇为犹豫。在“九阳豆浆机案”(24)中,被告(豆浆机销售商)的商品包装称仅用十几分钟即可喝上豆浆,事实上做好豆浆需要22分钟。在法院的判决中,认为只要是针对功能性的宣传有不实之处就足以使消费者产生错误认识,裁定存在欺诈,但对于该类产品究竟是否是以十几分钟出豆浆作为自己该产品主打功能则没有分析(25)。但是此类案件判决较少,法院体现出的倾向性不强,同时,针对“九阳豆浆机”一案,法院在其判决书中的论证也非常薄弱。进一步来讲,如果该部分虚假宣传容违反了法律文件,法院的态度则同样摇摆。在癌宝胶囊案中,原告在被告处购买“癌宝香菇多糖胶囊”,其包装上有文字描述:“适应人群:用于肺癌、肝癌、大肠癌、食道癌”,后发现该胶囊仅仅是保健品。法院审理后认为该产品是食品而非药品,但其包装盒上及产品说明书中使用了具有保健功能的用语和易与药用功能相混淆的用语,足以使消费者产生误解,构成欺诈(26)。而在前述党参蜂蜜案中,法院做出了相反认定。在该案中,除了前述宣传容外,原告诉称其包装上的药物批号实为食品批号,将此点也作为认定欺诈的缘由。法院则认为即使被告销售商品宣传容有所夸大或违反有关行政管理法规,系行政部门管辖畴,对于此种情形在认定欺诈时根本不予考虑(27)。从这两个案例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种功能上描述不实或混淆视听之意的案例中法院态度的不同:在销售者或者生产者对产品进行涵盖大量功能的宣传之时,若其中仅仅有个别功能失实或是语言有相对混淆之处,是否能够认定为欺诈,则应对消费者是否为真实意思表示进行分析。在简单的情形中,商品虽有诸多功能,但这些功能有的是消费者做出购买意思的真正目的,有的则仅仅是作为一种辅助性吸引而存在。一个正常的消费者在做出购买意思时,必须考察这个商品的本质功能有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而那些所谓“花里胡哨”的功能则难以对其本质意思构成影响。但在当前商品越来越多地出现复合功能的趋势下,对部分功能出现虚假宣传的情况,如何判断是否与其错误意思表示有因果关系,司法裁判仍有争议。
(三)特殊考量之一——行政处罚认定为欺诈的情形
经营者进行虚假宣传时,除了承担民事责任外,还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问题是,在行政机关已认定该行为为欺诈之时,法院是否可直接依据该行政处罚书认定欺诈?一些法院给出了肯定性的答复。在“伟刚诉丹尼斯百货案”(28)中,原告发现在被告处购买的数码相机产地与宣传不实,遂向市工商部门举报,后该局查实后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对被告作出罚款1万元的行政处分,法院在审理该案时明确指出“上述事实有工商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予以认定,被告的该销售行为已构成欺诈”。同样的,“极品羊肉卷案”(29)中,法院认为被告在其销售的产品包装物上标注“极品”字样,违反法律规定,可认定存在欺诈故意。
但另一些法院则认为该行政处罚认定的欺诈不等于《消法》中的欺诈。如“正军诉易初莲花公司案”(30)中,被告公司的一款创维产品使用了“极品”一词,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工商行政管理局对此行为做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31),认为被告在销售该商品时存在虚假宣传行为,而后原告据此诉至法院要求认定欺诈。而法院一审、二审均认为被告的宣传行为虽然存在一定的误导,但仅系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经营者虚假宣传的禁止性规定,该处罚书不能.够作为认定其构成旧《消法》第49条中欺诈的依据。“红檀木案”(32)和“丁家宜化妆品案”(33)等案中法院也持同样看法,将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区分开来。
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本来分属两个领域,同时,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7年《关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消费者申诉能否作出赔偿决定问题的答复》中明确指出了行政机关的处罚并不意味着民事责任的构成,因此,行政处罚认定的欺诈并不能够等于民事欺诈,法院在认定时仍需综合多方因素具体考量。
(四)特殊考量之二——知名品牌的特殊性
在市场上出现的诸多虚假宣传的案件中,有关知名品牌的案件往往具有特殊性。其市场份额大、社会影响广、品牌效应突出,消费者在购买这种商品的时候往往首先被其品牌吸引。这一情况使得知名品牌在进行虚假宣传时不仅带来了更为广泛的负面影响,也使此种虚假宣传行为认定欺诈的故意要件和因果关系要件更难判断。
在实务当中,法院对于知名品牌商品中虚假宣传的故意要件认定,态度较为保守。在“正军诉易初莲花公司案”中(34),其案情同“极品羊肉卷案”(35)和“极品酱品案”(36)极其相似,均系在营销过程中采用了“极品”这样的绝对化用语,违反了《广告法》的相关规定,但法院对三者采取了不同的态度(37)。在认定后两者案件时,法院认为:被告在其销售的产品包装物上标注“极品”字样,违反法律规定,存在欺诈故意,而对于第一个案件,法院认为被告系“知名品牌”,现有的证据(该案中证据证明力与另外两案相同)不足以证明被告具有“欺诈故意”。也就是说,对于类似的案件,法院在裁判时对于名牌产品认定欺诈时采取了更有利于经营者的态度。
同样的,品牌也影响到了法院对于欺诈认定时的因果关系判断。在上述“正军诉易初莲花公司案”中,法院在论证了不足以证明故意要件后,续称此种行为“对消费者的消费判断及选择是否产生影响及该影响对消费者权益的损害结果”仍需进一步的证据佐证。在“学顺诉国美案”(38)中,法院更是直接地表达了此种态度及原因。在该案中,原告从被告处购买一台海尔笔记本电脑,营业员明确告知被告该笔记本系生产,原告因信赖海尔电脑系生产而购买后发现实际产地为,诉至法院请求认定为欺诈。法院认为海尔作为国知名品牌,“其产地的差异对消费者的消费判断及选择是否存在影响及该影响对消费者权益的损害后果不明”,原告也未有明显证据进行佐证,故被告将产地错误标注不构成《消法》中认定的欺诈故意。
由上述比较可以看到,在对知名品牌涉嫌虚假宣传的案件中,实务当中很多法院对一般品牌采用某种不真实或者违反法律法规的宣传行为容易认定存在欺诈故意,而对知名品牌的夸大宣传,则认为这种品牌的效应本身就可使消费者产生购买的意思,因而在认定欺诈时更为保守。但这种行为是否合理,在未来的司法裁判中又该如何处理知名品牌虚假宣传认定欺诈问题?
四、何种虚假宣传行为构成欺诈
从司法实践的分析可知,虚假宣传认定欺诈的难点主要存在于故意要件、因果关系要件和产生错误认识要件的认定上,对于欺诈行为的判断上存疑不多。因此,笔者重点从前文提出的问题入手展开分析。
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之所以会对欺诈行为赋予无效或可撤销的效力规定,是因为它严重限制了交易相对人的意思自由,使得一方交易目的无法达成。因此,虚假宣传认定欺诈的程度可从两方面界定:从抽象角度来讲,消费者误解的后果应是其意思自由的限制和其本身的交易目的无法达成,仅仅对于一些交易中“无关紧要”且不会导致交易目的无法达成的宣传要素的误解理应排除出欺诈的围。另一方面,必须将判断因素具体到虚假宣传行为中分析,通过对现实判例的类型化讨论方能理清,关于这一点,笔者将从五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评价引人误解因素时应采客观标准
“消费者恐怕是世界上最挑剔的动物”,任何消费者都希望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该种“完美”的评价却是一种主观认识。那么,欺诈认定中错误认识要件的判断究竟应采主观标准还是客观标准,在笔者看来,客观标准的确立不仅从学理上更为合理,也更能够实现司法裁判的规化。
美国在判断“欺骗性广告”时的标准变化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中为了判断广告中的“欺骗性”标准,在1983年以前,采用的是“无知和易轻信的消费者”标准,然而这个标准过于保守,对于一方要求过于苛刻,随后其标准转化为“当时情况下合理行为的消费者”。[6](p14)同时,在德国,学者认为可采用经验社会学的方法,在具体的案件中由调查机构向1000名被选出的消费者进行询问,看他们如何理解有关广告,再计算出产生误导的百分比,10—15%的消费者产生误解就足够认定欺诈的存在了。[7]同时,澳大利亚的许多判例也考虑了如何处理因消费者未尽合理注意而陷于误解者的地位,提出“过分愚蠢之人不受法律保护”的观点,认为欺诈效果因为相对人的过失而中断。[8]
我国学者广乎认为,在进行错误认定时应采“客观标准”,即依据“欺诈是否可能使一个理性的普通人在施以平常注意力的情况下,是否可能产生误解来判断的”。[9]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在司法认定中,必须假设消费者对普通商品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否则法律将不得不强迫销售者对商品的缺点做出巨细无疑的述,并诉说该商品所有可能的危险性。换句话说,消费者仅仅以自身的认识为依据显然不足以确认欺诈。但如何在保障市场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兼顾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这就要对“判断能力”进行区分界定。
我国的司法实践主要将“判断能力”分为两种。对于一般的商品,固然以平均的认识程度(即常识)为准,
如蜂蜜的功效、喝酒不可能越喝越健康等。但是针对那些具有固定销售围的商品,则应以该种商品相关的消费者的认识水平为标准。在农用机械、种子、化肥等产品的销售中,就要以普通农民的眼光去看待其中的宣传行为,不能要求其如相对发达地区的消费者一样仔细阅读包装上的每个细节。该情况下,就可以相对的降低对欺诈行为认定标准,以保护特定消费者的权利。对于一些特定商品,除了常识要求之外,还应赋予消费者以谨慎义务。很多经济法学者反对这种谨慎的义务(当然甚至对错误意思本身也反对),认为这是对消费者责任的加重,不利于维护消费者的利益(39)。但是这仅仅是对谨慎义务的片面看法。须知,“在私法领域,权利是依法所主某种利益的可能性,义务为权利之反面,与权利具有对应关系。权利与义务指向同一利益,相应而生。”
[10](p18)如果在保护消费者的过程中仅仅强调消费者的权利和销售者的义务,不仅会损伤到商品交易的正常交易,而且在认定销售者的责任时也会没有依据。
需要注意的是,谨慎义务的设定同影响因素的判断标准一样,对于那些特定的消费者而言,其谨慎义务亦降低。在谨慎义务的认定上,对于通常的商品,其谨慎义务仅须达到常识即可,而对于那些数额巨大或关乎自身关键利益的产品,我们有理由相信有正常意识的消费者都会对商品仔细考量,认真判别。如上述“奇瑞汽车案”(40)中,对汽车的购买一般而言都是消费者较大的支出,消费者不可能仅仅根据销售者的盖然述,就断然做出购买的意思。而且销售者针对这种大额商品(如房产、汽车、精密仪器等)的宣传行为往往不是完全相同的,其不可能将这些不同类型的每一个细节都做出描述,往往是在具体的交涉中逐渐探究对方的购买意图。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销售者做出的行为能够使普通的消费者产生错误认识,也不能排除消费者在其中应有的注意义务。
更进一步地讲,这种倾向在商品房买卖过程中十分明显。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释》)中明确指出了在商品房买卖中应当认定为欺诈的情形(41)。虽然《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释》第9条并没有直言排除其他虚假宣传行为可以认定为欺诈之情形,但实际上,法院在裁判时除了强调消费者的谨慎义务外,偏向于从严认定商品房买卖中的欺诈行为,对该解释情形外的其他虚假宣传行为并不认定欺诈,而选择从《合同法》的途径解决案件问题(42)。因此,大量的案例判决均以该解释为依据进行裁判(43)。
因此,笔者认为,在错误认识的判断中应采“客观标准”,按照不同的商品或地域围,这种客观标准还有待司法裁判者进一步具体考虑。
(二)判断虚假宣传时应以主要功能为主
消费者对任何商品做出购买意思的原因无非是因为其能够满足自己的某种需要。那么,如果是部分满足的情况又该如何界定,这实际上是在市场宣传日益复杂的背景下,对欺诈构成要件中因果关系如何认定的问题,笔者从消费者的购买心理角度进行分析。
首先,对于和实际功能基本无关的虚假宣传,通常不宜认定为期诈。消费者在购买某件商品时的需多方面的,有些需和实际功能相关,有些则是和消费者的心理状态相关。如上述“九阳豆浆机”的案件中,该类产品的主打特色就是“快”,因此对于此类功能的虚假宣传可以认定为欺诈。
其次,对于商品中出现与基本功能“可能无关”(即消费者认为有关而生产者认为无关)的虚假宣传行为,应当依具体情况分析。一般来说,对于国的大部分产品而言,如果能够保证其功能的正常使用,且这些无关的虚假宣传与其品质在通常认识上没有联系的,都不应当认定为期诈。而对于那些较为特殊的产品,即使其虚假宣传并不与其功能相关,但足以使消费者做出错误意思表示的,也应当认定为欺诈。比如人参等珍贵药材,如果销售者将人工种植人参宣传其为正宗的长白山野生人参,即使其功能和价格没有区别,从常理而言也足以使消费做出购买意思。
最后,对于商品主要功能和次要功能的区分,笔者认为应以其是否能够影响到消费者的预期为主要判断因素。如果其主要功能是特殊的并且是其“主打”,而虚假宣传的功能仅仅是对商品的锦上添花,则难以认定其左右了消费者的购买意思。但如果这种主要的功能是一般产品都应当具有的,而此时次要功能的虚假宣传很有可能会主导消费者的错误意思,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由法院根据具体的情况去认定欺诈行为的成立。
(三)行政处罚认定欺诈的证据效力
我国现行规定中在关于虚假宣传的行政责任认定上,除《产品质量法》第59条规定“在广告中对产品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