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下)期末考试卷(附答案解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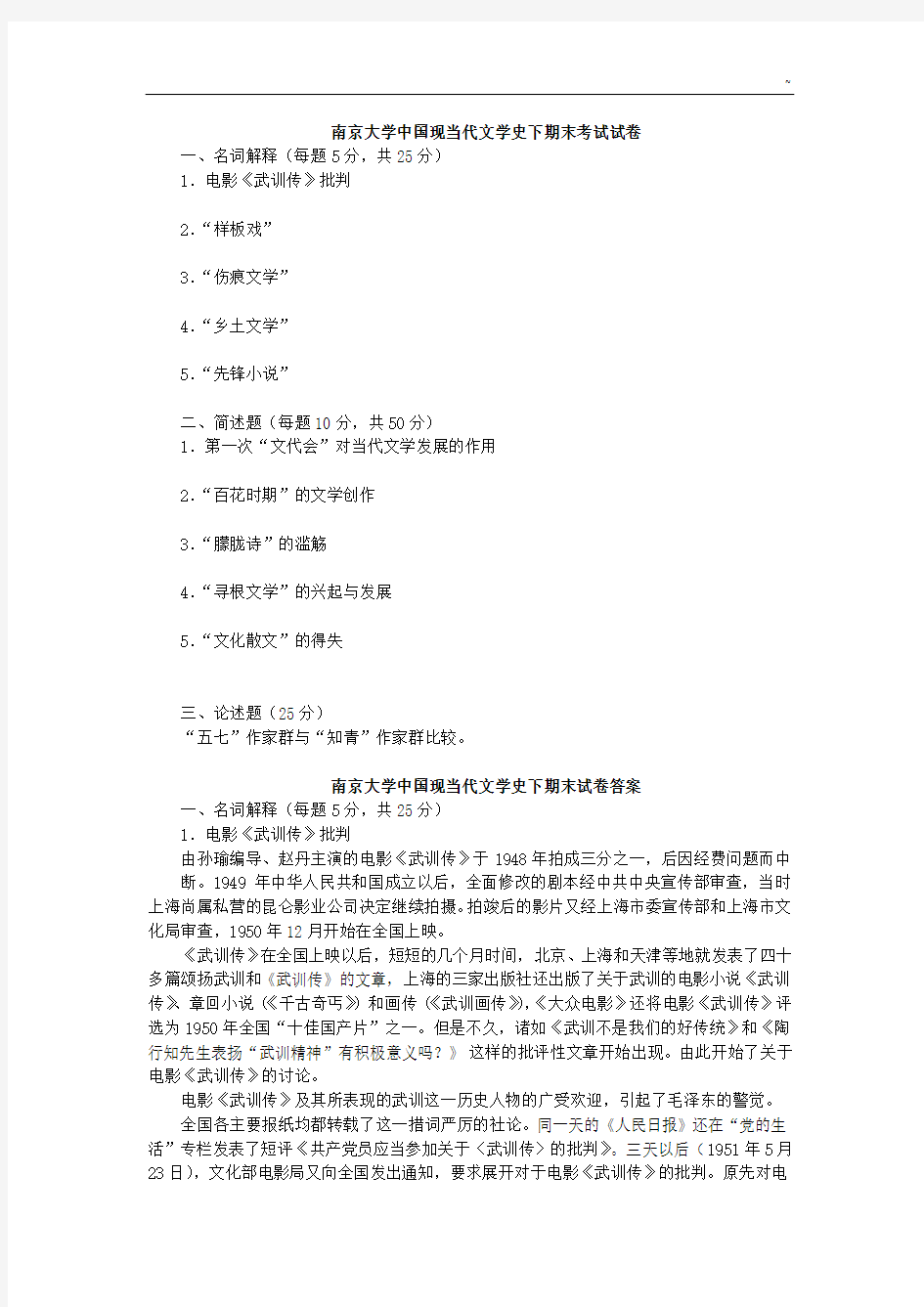

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下期末考试试卷
一、名词解释(每题5分,共25分)
1.电影《武训传》批判
2.“样板戏”
3.“伤痕文学”
4.“乡土文学”
5.“先锋小说”
二、简述题(每题10分,共50分)
1.第一次“文代会”对当代文学发展的作用
2.“百花时期”的文学创作
3.“朦胧诗”的滥觞
4.“寻根文学”的兴起与发展
5.“文化散文”的得失
三、论述题(25分)
“五七”作家群与“知青”作家群比较。
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下期末试卷答案
一、名词解释(每题5分,共25分)
1.电影《武训传》批判
由孙瑜编导、赵丹主演的电影《武训传》于1948年拍成三分之一,后因经费问题而中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全面修改的剧本经中共中央宣传部审查,当时上海尚属私营的昆仑影业公司决定继续拍摄。拍竣后的影片又经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上海市文化局审查,1950年12月开始在全国上映。
《武训传》在全国上映以后,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地就发表了四十多篇颂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上海的三家出版社还出版了关于武训的电影小说《武训传》、章回小说(《千古奇丐》)和画传(《武训画传》),《大众电影》还将电影《武训传》评选为1950年全国“十佳国产片”之一。但是不久,诸如《武训不是我们的好传统》和《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意义吗?》这样的批评性文章开始出现。由此开始了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电影《武训传》及其所表现的武训这一历史人物的广受欢迎,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
全国各主要报纸均都转载了这一措词严厉的社论。同一天的《人民日报》还在“党的生活”专栏发表了短评《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三天以后(1951年5月23日),文化部电影局又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展开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原先对电
影及武训其人的肯定性评论迅速从报刊上销声匿迹,代之而起的,只是一味的、在思想立场和思维方法上与“社论”完全一致的批判。周恩来和周扬等曾经支持或未阻止过这部电影的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检讨,当时的上海市文管会副主任兼文化局局长夏衍还在1951年8月2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的检讨。这样,起初局限于文化艺术领域的正常的“学术讨论”就被“升级”为规模巨大的政治批判运动。全国的所有报刊都在批判武训及《武训传》,不同的意见根本无法表达,电影《武训传》的编导、演员和曾经肯定过武训的人,均都被迫进行了检讨,有的地方甚至还搞人人过关。《人民日报》1951年7月23日至28日发表“武训历史调查团”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和8月8日发表周扬《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电影〈武训传〉批判》,算是在形式上为这一批判运动做了总结。经过毛泽东精心审改的《武训历史调查记》这样为武训定性:“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难道还不确切吗?”进而强调:“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代了,用武训这具僵尸欺骗中国人民的恶作剧应当结束了,被欺骗的人们也应当觉醒了。”
毛泽东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并不仅仅因为对武训这个历史人物和这部电影的评价问题。更为深层的原因在于武训和《武训传》在当时的广受欢迎所显示出来的政治文化意识和毛泽东所欲建立的新文化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电影《武训传》以武训的“行乞兴学”反衬了太平军武装斗争的失败,这样一种政治意识,为刚刚通过农民造反式的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毛泽东所难以接受。电影《武训传》虽然是当时尚未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私营制片公司所拍摄,但其剧本审读、资金投入、最终审查的获得通过和在领导层的内部放映,以及在全国公映后的社会反应,在毛泽东看来,都显示出很多共产党员甚至是不少领导干部的“思想麻痹”,这使得在政治上与文化上都极为敏感的毛泽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另一方面,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还有着另外的目的,这就是接续了第一次文代会开始的对于来自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清理,周恩来便曾明确指出《人民日报》社论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认真学习,提高思想水平”,而电影《武训传》的主要创作者正是来自于1949年以前的国统区。
毛泽东所发动并且在全国所展开的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执政党领袖凭借其所特有的政治权威与精神权威,充分运用高度组织化的文化管理体制,在文化官员的密切配合下所进行的广泛的社会动员。作为在1949年以后初次展开的大规模的具有明显激进色彩的文化实验,它的基本“经验”与运作模式在其后的批判运动中都有明显的延续,所以说,它为后来文学领域的批判运动开了一个“先例”。
2.“样板戏”
在戏曲舞台上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受到批判的同时,京剧现代戏运动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文化部直属单位和19个省、市、自治区的28个剧团参加,演出了《芦荡火种》、《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等37个剧目。毛泽东有选择地观看了部分剧目并接见演职人员。后来这些被毛泽东看过的剧目被投入众多的人力物力进一步完善。这次大规模的会演,推动了京剧现代戏的“样板化”。
江青紧紧抓住了京剧现代戏运动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可以说,正是京剧的程式化、脸谱化等特点,为江青假手京剧改革推行文革政治理念提供了可能。
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1967年5月1日起,中央文革小组安排上海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芭蕾舞剧《白毛女》和山东的《奇袭白虎团》,会同北京的《红灯记》、《沙家浜》,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
家浜》在北京举行了会演,历时37天,演出218场。这八部作品后来被称为八个“样板戏”。这些“样板戏”被认为“不仅是京剧的优秀样板,而且是无产阶级文艺的优秀样板,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各个阵地上的‘斗、批、改’的优秀样板。”连续二十多天,《人民日报》《红旗》等不断以醒目的版面发表“样板戏”的剧本、剧照。6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会演结束,号召“把革命样板戏推向全国去”。从此,“唱样板戏,做革命人”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样板戏”成为“阶级斗争”的强大动力。为了大规模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样板戏运动”被赋予严格的规范性。第10期《红旗》撰文提出要“学习革命样板戏,保卫革命样板戏。”文章称,演出“样板戏”,一句台词、一个台步、一束灯光、一个道具,甚至人物身上的一块补丁都不能变动,否则就是“破坏革命样板戏”,就要“举起无产阶级专政的铁锤,坚决打击破坏革命样板戏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样板戏”走进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担负起特殊的政治使命。
第一批样板戏之后,根据“样板戏”范式生产的戏剧作品不仅数量极其有限,而且情节公式化、人物脸谱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在戏剧文学上日益陷入“死胡同”。为了继续向民众灌输“文革”意识形态,同时营造“文革”文艺的虚假繁荣,1970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文艺短评《做好普及革命样板戏的工作》,从而掀起了一场全国范围的“样板戏”普及运动。“样板戏”普及运动的内容有:中国京剧团、北京京剧团、上海京剧团、山东京剧团等创造“样板戏”的“样板团”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传播“样板”;全国各地各级的京剧团无一例外地复制“样板”,其它剧种的艺术团体也都要积极地移植“样板”;使用电影手段复制并传播“样板戏”的舞台演出;在基层开展“样板戏”的业余演出。由于“样板戏”几乎是当时惟一准许演出的戏剧,而戏剧活动在当时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十分匮乏的条件下又是人们娱乐的主要方式,一时间,遍及全国的乡镇、工厂、学校都曾涌现过自己的李玉和、李铁梅、阿庆嫂……
从1966年到1972年的6年间,全国没有生产出一部故事片,拍摄“样板戏”的舞台艺术片是这段时间电影艺术家惟一能够开展的电影“艺术”活动。为采用电影的方式普及“样板戏”,中央警卫部队的“军宣队”进驻了北京电影制片厂,一批知名电影导演和摄影师被“解放”了出来。江青亲自为“样板戏”的电影制作制定了“还原舞台,高于舞台”的原则。这个原则的含义是:首先,必须忠实于“样板戏”演出的舞台形式,不搞实景拍摄,禁止主观镜头,反对电影化,维持观众的剧场感、舞台感,防止镜头艺术的真实性消解戏曲的假定性。其次,利用电影技术,如镜头、视角、用光、构图、“蒙太奇”等手段,把“三突出”的“样板戏”创作原则再推进一步,使银幕英雄比舞台英雄更高大、突出,使“阶级敌人”比他们在真实的舞台上更丑恶、渺小。
美术、曲艺、小说、诗歌等领域,学习和借鉴“样板戏”经验的运动也逐步展开。直至1971年,“样板戏”一直垄断着文坛。“样板戏”盛行的同时,“文革”最残酷的斗争狂潮也在涌动,在各种抄家、批斗等活动中,常常伴随着“样板戏”的演出、播放,“样板戏”中的斗争模式、话语方式常常潜在地影响着参与造反的青年人,巴金后来说过:“谁不知道‘四人帮’横行十年就靠这些‘样板戏’替它们作宣传,大树它们的革命权威……大家不是看够了‘李玉和’、‘洪常青’们在舞台下的表演吗?”
3.“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概念所指称作的创作,主要是小说,尤其是中、短篇小说,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也与伤痕小说概念等同。“伤痕文学”是一批深刻地控诉十年动乱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和心灵创伤的作品的涌现,这批小说被称为“伤痕文学”。“伤痕文学”的主体是短篇小说,包括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陈国凯的《我该怎么办》、王蒙的《最可宝贵的》等。以叶辛的《蹉跎岁月》、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为数不
多的长篇小说,也是“伤痕文学”中的成绩突出者。“伤痕文学”中还有一类作品,它们以讴歌革命战士坚持斗争、不屈不挠的高风亮节为主题;从维熙的被人称为“大墙文学”,取材于监狱生活的系列作品,是这部分小说的代表。《大墙下的红玉兰》是从维熙的代表作。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张贤亮的《土牢情话》、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等作品,是以赞美人民美好情操为主题的“伤痕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伤痕文学”亮出“伤痕”后,接下来自然就是对历史悲剧根源的探寻。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首先反思了极“左”思想的危害。此外,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刘真的《黑旗》、张弦的《记忆》、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王蒙的《蝴蝶》、古华的《芙蓉镇》等等,都是对历史事实的深入回顾思考,因此它们被称为“反思文学”。1979年,正当“反思文学”方兴未艾之际,蒋子龙以他特有的敏锐感觉和出色才识把目光投向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他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以振聋发聩的思想和艺术力量,为新时期文学开拓了一片新的天地枣“改革文学”。很快,“改革文学”的大旗下便聚集了一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蒋子龙除《乔厂长上任记》之外,又陆续发表了《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等。此外,还有柯云路的《三千万》、《新星》、《夜与昼》,水运宪的《祸起萧墙》,张贤亮的《龙种》、《男人的风格》,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5号》,陈冲的《无反馈快速跟踪》,张契的《改革者》,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和《浮躁》等。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各条战线的人们不畏艰险、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
4.“乡土文学”
从70年代末开始到80年代,“乡土文学”在台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追溯一下1977年爆发的第二次“乡土文学论争”的历史背景。众所周知,台湾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是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台湾最活跃的时期。从1953年开始,国民党当局依赖美、日的援助,经济开始发展,但对外依赖性相当大。至1970年钓鱼岛事件发生,1971年台湾失去联合国席位,1972年尼克松访问大陆,日本与台湾断交,这些都给台湾人很大震动,并刺激他们检讨过去对外过分依赖的失策,于是对“洋”的崇拜失落了,弥觉“土”的可贵。因此到七十年代,一个以“乡土文学”为指称的,以关怀台湾本土现实和弘扬民族精神为主要内容,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方法的文学思潮开始兴起,并且逐渐居于这一时期文学的主导地位。它的出现是对一向用“反共”标签来箝制言论的当局文化专制主义和迷失了自己民族归属和社会责任的现代主义的反拨,也是当代台湾文学发展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至80年代,乡土文学的实绩进一步显示出来了。如杨青矗的《龟爬壁与水崩山》反映由剥削制度所导致的贫富悬殊是台湾社会的普遍现象。王拓的《金水婶》描写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如何冲击传统的社会美德。黄春明的《溺死一只老猫》表现资本主义与农村自然经济、传统观念发生的冲突;《我爱玛莉》在揭露和讽刺洋买办、崇洋媚外的同时,表现民族意识的觉醒。而且这些乡土文学中还成功地塑造了足以反映历史发展的众多小人物的生动形象,如陈映真《将军族》中既深深相爱,又双双殉情的大陆人三角脸和本省人小瘦丫头;《夜行货车》中最后觉悟起来,在洋人面前用台语向自己同胞说“在蕃面前我们不要吵架”,“我是再也不要龟龟琐琐地过日子”的詹奕宏;杨青矗《下等人》中当了三十年临时工,被解雇前夕,想以“因公殉职”弄到退休金,好使九十岁老父生活有个着落而故意撞车死去的董粗树;黄春明《锣》中既聪明善良又愚昧狡黠,既自负又自卑,使人不由得联想到阿Q 的憨钦仔等。显然,台湾乡土文学是以乡土为旗帜,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旨在对专制政治和阶级不平进行反抗和揭露的。
5.“先锋小说”
“先锋小说”的具体所指,在当时和现在是有一定差异的。当时它基本上指马原、洪峰、
格非、余华、孙甘露、苏童、叶兆言等,但却不包括残雪、莫言等,而近来文学史有将这两者合并论之的趋势。如果按后一种选择,那么也许可以把先锋写作分成三种类型:一类以残雪、余华、洪峰为代表,另一类以莫言为代表,再一类主要由马原、格非、孙甘露、苏童构成。在这三类中,也许第一类会引起最多的不同意见,但正是这一类最富现代主义艺术的批判性。表面上,残雪的梦魇叙述、余华阳光下的死亡高蹈、洪峰对马原的模仿各不相同,但他们对超现实意象压抑的展示、死亡的不动声色的呈现、局外人般的混沌自我,一起指向人之存在的荒谬性和非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与前面所讨论过的“现代派”小说是一致的。无疑更易于从灰冷、阴暗的角度,影响人们的情感和对现实的理解。而相对而言,后两类就要与这种文化哲学意义上的现代主义特色较远,更多地指向叙事变革的形式化一极。莫言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一些文本,如《透明的红萝卜》、《球状闪电》、《爆炸》等,有故事,也有较为完整的情节,但其着眼点显然不在于展现存在的荒谬、残酷,而在于某种特殊的叙述感觉的追求。它既与现代文学史上的“东北叙事”(典型的作家是萧红)遥遥相关,更是《百年孤独》式的“魔幻现实主义”中国式的呈现。所以它所带来的阅读效果,就更重在独特文学审美感受的体悟,而远离存在意义上的哲学深思。所以,实际上,人们承认莫言对小说叙事探索的贡献,但却极少将其归入先锋小说家的行列。第三类的马原、孙甘露等,才将小说叙事推向近乎纯粹化的叙述实验、语言实验。对于这样的文本,要想进行什么深度意义的挖掘,就很困难了,可能最多只能联系性地说,这种对故事、对意义的放逐、甚至对阅读的拒绝,是对传统小说观念的彻底颠覆。然而如果小说彻底放弃了故事的讲述、放弃了对任何存在意义的探究,小说也就要死亡了,由其所产生的颠覆性的联想,也就会很容易地流于纯粹的语言游戏。
二、简述题(每题10分,共50分)
1.第一次“文代会”对当代文学发展的作用
第一次文代会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学的全面领导,确立了新生政权与文学艺术家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主/客体关系。毛泽东7月6日的即兴讲话虽然简短,却很深刻地隐含了这种主/客体关系:“同志们,今天我来欢迎你们。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我们欢迎你们”。这一讲话所频繁使用的“你们”和“我们”这样的字眼充分显示出,在毛泽东的思维当中,掌握政权的主体“我们”并不包括被称为是“你们”的文学艺术家,“你们”尚未真正进入“我们”的阵营,而且,只是因为“你们”合乎人民和革命的需要,才为“我们”所欢迎。实际上,中共中央的“祝辞”由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来作,特别是周恩来的政治报告中所详述的人民解放军在新政权的建立中所建立的赫赫功勋,也必然会使亟待改造的文人们自惭形秽,产生某种自卑心理。
从五四前后和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战中通过思想倡导的方式对于文学实践的极力介入,中经三十年代通过“左联”而对文学实行的“组织化”实践,到四十年代以延安为中心的地区依托于政权对文学的管制,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学领域的介入,终于发展为“国家”层面上的全面领导。从此,整个国家的文学实践便被完全纳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实践之中,中国共产党可以动用包括国家机器在内的一切资源与力量对文学提出形形色色的政治或政策要求,进行相当有力的掌控。
第一次文代会确定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方向。郭沫若在开幕词中认为毛泽东的《讲话》“一直是普遍而妥当的真理”,并且“明朗地表示”要“把这一普遍而妥当的真理作为我们今后的文艺运动的总指标”。周扬的报告却说得更加
断然而干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于是,“大会宣言”便指出:“今后我们要继续贯彻这个方针,更进一步地与广大人民、与工农兵相结合”。在这样的基本方针明确之后,关于文艺工作者的深入生活、文艺的普及与提高、旧文艺的改造以及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方面的具体政策便都有了相当具体的规定。
大会产生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和周扬为副主席。成立了中国文联所属的包括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在内的文学、戏剧、音乐、电影、美术、戏剧改革和曲艺等方面的专业团体。
第一次文代会建立起来的由各种团体所组成的文学体制一直延续至今。这些团体名义上是“群众团体”的性质,但在实际上,它的任务却是与“政权机构里面的文艺部门”一样并且与后者紧密配合,“安排”和管理全国的文学工作。周恩来的政治报告在谈及此点时曾向大会指出:将要成立的新的国家政府机构中,“也要有文艺部门的组织。这种文艺部门的组织,那就要依靠我们上面说的那些群众团体来支持”,“我们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机构里面的文艺部门,也需要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来积极参加工作”。“文艺工作在政府方面也好,在群众团体方面也好,我们都要来有计划地安排。这就靠你们将要推选出来的领导机构来安排这些事情”。中国共产党利用其所建立的文学体制与政府文化领导机构一起来试图“有计划地安排”和组织文学生产,在周恩来的政治报告及其在后来的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1961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这一点,均都有着一以贯之的体现,这也使得国家对于文学事业的领导非常类似于经济工作,成了一种“计划文学”。
周恩来等人的报告中强调,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意味着来自不同方面的文学艺术人士的“大团结,大会师”。“团结”、“会师”也是会议文件所屡屡强调的会议主题。但是,这种“团结”与“会师”,却有着相当明确的前提条件。关于这一点,周恩来的政治报告指出:“这次文艺界代表大会的团结是这样一种情形的团结:是从老解放区来的与从新解放区来的两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也是新文艺部队的代表与赞成改造的旧文艺的代表的会师,又是在农村中的,在城市中的,在部队中的这三部文艺军队的会师。这些情形说明了这次团结的局面的宽广,也说明了这次团结是在新民主主义旗帜之下,在毛主席新文艺方向之下的胜利的大团结,大会师”。这里的“旗帜”与“方向”,显然是“团结”与“会师”的前提与基础。
实际上,在政治报告所说的“情形”之外,还有着另外两个方面的“情形”:
一方面,第一次文代会“团结的局面”虽然很“宽广”,但其代表制度及其所建立的文学体制毕竟有着突出的排异性。很多在现代文学史上极有成就的作家被排斥在边界之外。1948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已胜券在握时,为了强化其对文艺的领导,在香港创办了一份在当时震动文坛的刊物——《大众文艺丛刊》,这一刊物的主要作者,均是在当时或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或中央政府主管文艺工作的文化官员,如冯乃超、胡绳、林默涵、夏衍、郭沫若、茅盾等人。一个引人注目的动向是,《大众文艺丛刊》所发表的文章不仅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文化意志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更有基于这样的意见所展开的对于不少作家的批判。《丛刊》第一辑所刊郭沫若的文章《斥发动文艺》,以一种粗暴、霸道的方式,将沈从文、朱光潜和萧乾等人的创作指斥为“反动文艺”,挖苦他们是“桃红色”、“蓝色”和“黑色”的作家。果然,第一次文代会多达七八百人的代表当中,没有了沈从文、朱光潜、萧军、端木蕻良和冯文炳这样的作家。郭沫若在文代会作总报告的时候,甚至多次点名指斥萧军。这种依托于政治力量尤其是大一统的政权力量对作家的排斥,不仅明显侵犯了文学的尊严,其对作家的精神生命与创作生命的损害,无疑也相当严重。
另一方面,即使是在文学体制的内部,也有着相当明显的等级关系。来自于“老解放区”的作家在精神与思想上分明要比那些来自于当时的“新解放区”(即原国统区)的作家处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