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楚辞的比较分析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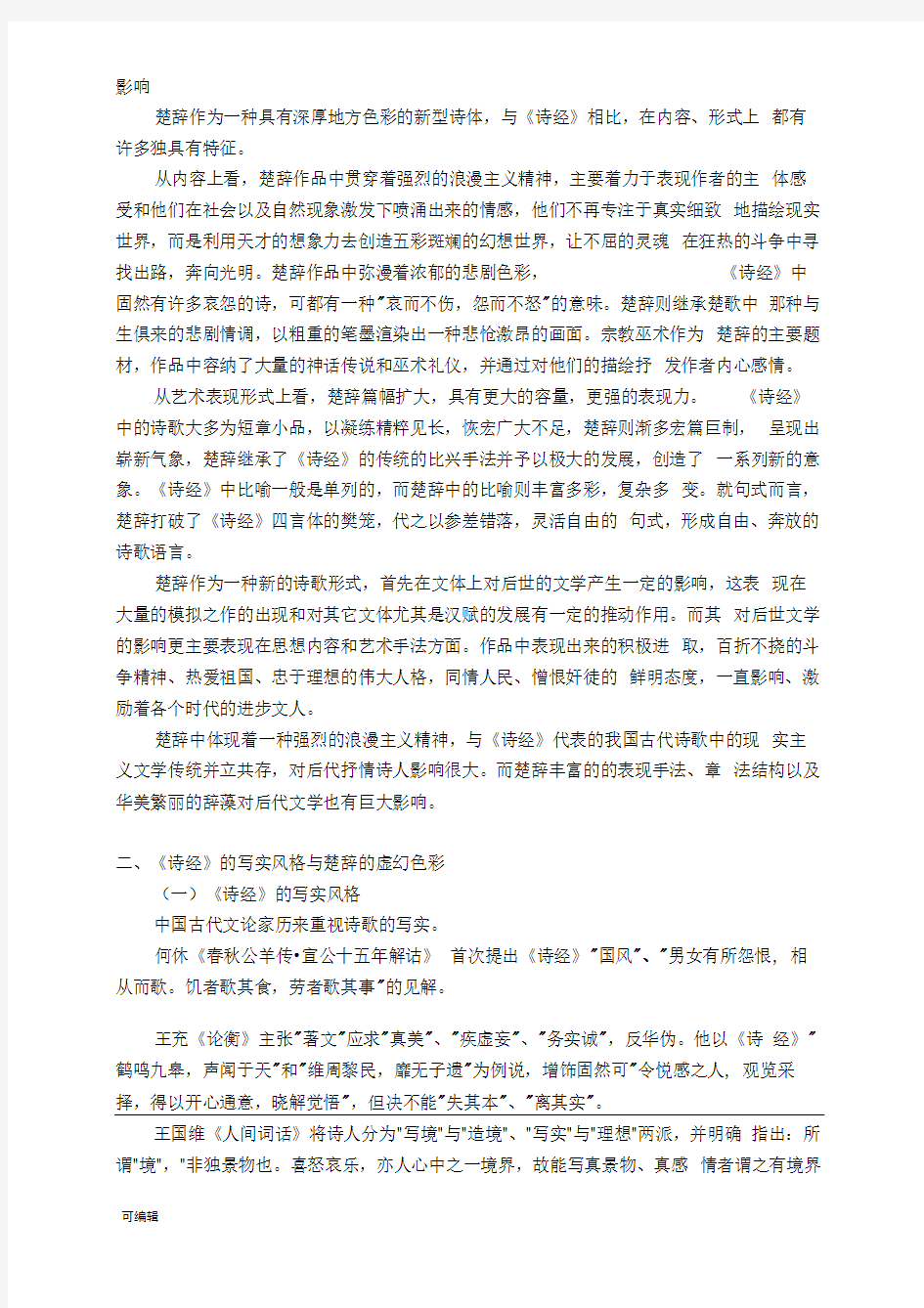
《诗经》与楚辞的比较分析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它的出现以及它所达到的高度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使其在我国和世界文化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楚辞以其思想上的博大精深、艺术上的精美富丽深受世人的瞩目,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堪称典范,以至在其以后的诗歌发展史上形成了一个浪漫主义的艺术表现与爱国主义的献身精神相结合的优秀传统。《诗经》和楚辞所代表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对后来的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的作者在学习中对诗、骚作了一些研究,现就二者之间的表现手法、主题、审美等作粗浅的比较。
一、《诗经》、楚辞比较综述
《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约五百年间诗歌共三百零五首。最初只称为《诗》或《诗三百》,直到汉代学者们把它奉为儒家经典之一,始称为《诗经》。《诗经》中的作品本来都是要以由乐器伴奏演唱的乐歌,所以《墨子?公盂篇》说:"弦诗三百,歌诗三百。"它根据音乐的不同而分为风、雅、颂三部分, 其中雅又分为大雅、小雅。
《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这些优秀的篇章,确立了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坚实基础,对后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从汉魏乐府到近代民歌、民谣的历代民歌是它的嫡传。同时,《诗经》对历代文人的创作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它启发诗人与作家以文学为手段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关心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抵制脱离社会内容、单纯追求形式的形式主义倾向,推动了诗坛的健康发展。《诗经》在艺术表现上对后代诗歌的影响也很大。它树立了一种朴素而优美的风格,不事雕琢,而是选择准确、生动的语言刻画各种事物,尤其是通过具体生动的形象寄托复杂的感情的比兴手法,向来被后代诗人所称道、继承和发扬,在我国诗歌创作中形成了一个传统。
楚辞是战国后期形成于楚国的一种新型诗体,是继《诗经》之后出现在我国诗坛上的又一诗歌高峰,楚辞的产生和形成与《诗经》不同,其有着古老的根源和复杂背景。首先,楚国民歌是楚辞产生的直接源头。楚国民歌与中原地区流行的民歌在音调、句式、韵律以及风格、情致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是同楚辞有明显的沿承关系,楚辞不过是扩展了的文人化的楚歌。其次,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的楚文化是楚辞产生的摇篮。当然,楚辞在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就诗歌而言,代表着中原诗歌最高成就的《诗经》不仅是北方各诸侯国家从事外交活动的辞令规范,教育子弟培养人才的典章和教材,也深受江淮流域诸国的重视和喜爱。战国时,能够赋诗言志的楚国政客文人很多,屈原作为楚国的一个高层知识分子,对《诗经》无疑是相当精熟的,因此,他的许多作品如《天问》、《橘颂》等在形式体制上深受《诗经》
影响
楚辞作为一种具有深厚地方色彩的新型诗体,与《诗经》相比,在内容、形式上都有许多独具有特征。
从内容上看,楚辞作品中贯穿着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主要着力于表现作者的主体感受和他们在社会以及自然现象激发下喷涌出来的情感,他们不再专注于真实细致地描绘现实世界,而是利用天才的想象力去创造五彩斑斓的幻想世界,让不屈的灵魂在狂热的斗争中寻找出路,奔向光明。楚辞作品中弥漫着浓郁的悲剧色彩,《诗经》中固然有许多哀怨的诗,可都有一种"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意味。楚辞则继承楚歌中那种与生俱来的悲剧情调,以粗重的笔墨渲染出一种悲怆激昂的画面。宗教巫术作为楚辞的主要题材,作品中容纳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和巫术礼仪,并通过对他们的描绘抒发作者内心感情。
从艺术表现形式上看,楚辞篇幅扩大,具有更大的容量,更强的表现力。《诗经》中的诗歌大多为短章小品,以凝练精粹见长,恢宏广大不足,楚辞则渐多宏篇巨制,呈现出崭新气象,楚辞继承了《诗经》的传统的比兴手法并予以极大的发展,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意象。《诗经》中比喻一般是单列的,而楚辞中的比喻则丰富多彩,复杂多变。就句式而言,楚辞打破了《诗经》四言体的樊笼,代之以参差错落,灵活自由的句式,形成自由、奔放的诗歌语言。
楚辞作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首先在文体上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一定的影响,这表现在大量的模拟之作的出现和对其它文体尤其是汉赋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而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更主要表现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方面。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积极进取,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热爱祖国、忠于理想的伟大人格,同情人民、憎恨奸徒的鲜明态度,一直影响、激励着各个时代的进步文人。
楚辞中体现着一种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与《诗经》代表的我国古代诗歌中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并立共存,对后代抒情诗人影响很大。而楚辞丰富的的表现手法、章法结构以及华美繁丽的辞藻对后代文学也有巨大影响。
二、《诗经》的写实风格与楚辞的虚幻色彩
(一)《诗经》的写实风格
中国古代文论家历来重视诗歌的写实。
何休《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首次提出《诗经》"国风"、"男女有所怨恨, 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见解。
王充《论衡》主张"著文"应求"真美"、"疾虚妄"、"务实诚",反华伪。他以《诗经》"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和"维周黎民,靡无子遗"为例说,增饰固然可"令悦感之人, 观览采择,得以开心通意,晓解觉悟",但决不能"失其本"、"离其实"。
王国维《人间词话》将诗人分为"写境"与"造境"、"写实"与"理想"两派,并明确指出:所谓"境","非独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
"。
这些论述可以说道出了写实诗歌的一些本质方面,但用以评说《诗经》,则还说不
上全面、准确。我们以为对《诗经》的写实风格,应从写实精神和写实方法两个方面看。
所谓写实精神,主要表现在真实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尖锐、深刻地触及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本质,具体、生动地表现了广大人民的思想、爱憎。简而言之,就是所谓广泛性、深刻性、人民性。
所谓写实方法,我们以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有感而发,为情造文。
刘勰《文心雕龙?情采》曾将作家的创作态度分为"为情而造文"和"为文而造情" 两种情况,并认为"昔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 .......... 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
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这是很符合"国风"中的民歌谣谚和"小雅"中的仕官怨诽的。
《唐风?林杜》是一个孤独的流浪者的自叹。杜梨独立,对于后边的"独行踽踽"
来说,既是兴,也是比。诗人之所以反复慨叹自己独行在外,无人资助,必是身历奔波之苦和世态炎凉,且体会颇深的。至于为何奔波,因何孤独,虽然难以确道,但因情而咏,为情造文,却是肯定无疑的。
《小雅?北山》是"士者所作,以怨大夫"(姚际恒《诗经通论》)。"怨"从何来?一曰"朝夕从事、不得休?quot;;二曰"王事靡盬,忧我父母";三曰分工"不均","我从事独贤";四曰劳逸不均,令人气愤。都是作者亲历亲受。没有"经营四方"的劳苦、忧愁,没有对不合理的现实的深怨不满之情,何来如此怨刺之作。
第二,选材典型,开掘深入。
《卫风?氓》所叙述的妇女被弃事件,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这首诗的深刻和可贵之处,主要并不在刻画了一善良勤劳、性格坚强的弃妇形象,而在于写出弃妇已把对丈夫个人卑劣行为的怨愤,提高到了"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的高度,说明她已从自身的悲惨遭遇中认识到男人和女人在恋爱婚姻问题上的不平等,从而触及到了当时普遍存在的社会现实。这就把斥责、批判的锋芒,指向了造成这种不合理现象的罪恶的夫权制,指向了把妇女压在最底层的黑暗社会。
《小雅?小文》是一首士大夫怨刺诗。从全诗以怨天发端("旻天疾威敷于下土")来看,诗人怨愤已积之甚久。怨什么呢?不是一般地怨生逢时,家国多难,个人遭遇不幸,而是直触国难民灾之所由来:执政者重用奸愚,拒善从恶;众小人党同伐异, ' 谋犹回遹"。诗人政治洞察力的敏锐、超前,诗歌政治讽谕力的尖锐,深刻是很值得称道的。
第三,如实展现,较少夸饰
《唐风?椒聊》是赞美一个妇人的。每章首末的"椒聊达之实,蕃衍盈?quot;、
椒聊且,远条且",虽是触物此类,言其香、美和善于生育,但未风夸饰。
硕大无朋"、"实大且笃"亦是用朴素、恬淡之语,誉其外表之美和内在性格之美,既无一点夸张,也不着秾艳色彩,朴实得没有一丝一毫雕刻。
第四,舌端直言,质朴无华
《鄘风?相鼠》是一首讽刺、诅咒品行不端、淫乱无耻之徒的诗。王世贞认为这首诗"太粗"。其实,语言粗直,正是这首民俗歌谣的特点和优点。直面现实,怨而且怒;一吐为快,毫无遮拦,正是嫉恶如仇的正直之士的性格必然。况且这恶之欲其死的愤恨,并未流于一般的谩骂,何"太"之有!
《郑风?山有扶苏》是一首具有独特风光的爱情诗。它既不是直言其爱,也不是直抒其怒,而是采取一种歪曲的形式:戏弄笑骂,似怨而实爱。"不见子都,乃见狂且",
语言何等粗直,何等明白,而又何等富有情趣,何等耐人寻味,"言有尽而意无穷"。
论述至此,关于《诗经》写实风格的方方面面,我们都已说到了。剩下的问题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同是先秦诗歌,南楚歌词(楚辞)是那样天真烂漫,富于幻想,而中原乐歌(风雅)何以如此凝重质实,富于理性这得从文学之外的政治环境、地理环境、民风民俗、文化氛围上找原因。
从政治环境看,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是华夏民族的腹地,是商、周王朝的统治中心。相对于那些天高皇帝远的"四方蛮夷",这里是王朝直接统治、控制的地方,是各种宗法制度、政治高压、邪恶势力所带来的影响最强、危害最剧的地方。地位的不平等、贫富的悬殊、吃人与被吃等等黑暗不合理的现象,在这里是无处不有,集中而严重的。司马迁讲过一句合乎情理的老实话:
从地理环境看,长江以北,黄河流域的中原地方,虽土地平阔,一望无垠,但物产并不丰富;虽也有些不高不陡的山脉,但多穷山秃岭,"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古代并不能给他们带来温饱。自然条件的艰苦、恶劣,不仅给他们的肉体带来许多痛苦,也给人们的心理蒙上一层阴影,使他们在"人祸"之外又多了一种"天灾"的忧患。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民歌谣谚,怎么能不带有这种环境、生活、心理上的印痕而天真烂漫呢!从民风民俗看,中原人向来不似南人妖艳轻浮,华而不实,而是质朴实际,比较理性。
他们习惯于实事求是地面对自己周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较少去做那些不切实际,想入非非的美梦。一些年轻学者总喜欢搬用西方人对中国国民性的分析,笼而统之地谈论什么中国人"重实轻玄","非常实利主义","摒绝杳渺玄想"。事实上,真正称得上" 重实轻玄",而较少浪漫空想的,只是中国人中的中原人。中原乐歌《诗经》之多写实而少虚幻,正是这种民风、民俗的反映。
从文化氛围看,《诗经》诞生前后,在中华民族的腹心地带,汉民族意识形态发展的总趋势、总倾向,是理性主义。先秦各派思想家,不论是儒家、名家、法家、墨家、还是道家,都在用理性主义精神来重新解释古代原始文化,把人对异化了的神怪偶像的
崇拜引向对现实主义社会,现实人生的思考。感于哀乐、缘情而作的"国风"、"小雅",
正是以写实的艺术形式体现了那时代中原文化的理性精神,而与氏族社会结构残留较多,神州巫术观念尚未被理性化、人间化的南梦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梦辞,自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二)楚辞的虚幻色彩
说起虚幻,人们自然会想起远古神话。因为"神州形象体现出人们一面试图虚幻地改造周围世界,一面力求解释周围事物,揭示其起源"。总之,体现了艺术幻想的最初萌芽。《诗经》虽然是我国最早的语言艺术品,但由于它是产生在理性早熟、史官文化统治的中原地区,人们却艰难从中看到远古神州所具有的那种"虚幻"的幻想的瑰丽色彩和艺术魅力。只有产生于开化较晚的蛮夷之地,脱胎于巫术文化的楚辞,才以它那古拙而浪漫、狞厉而神幻的艺术境界,使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原始艺术的美。
与其所表现主题"当代"性相伴随,《诗经》的题材是取诸自作者身边的。由于《诗经》发展了远古歌谣和神话传说的传统,扬弃了那种虚幻、幼稚的想像,面向生活,以广阔的社会生活为题材,进行真实而细致的描写,不少诗篇都具有一定高度的典型性,成为那个时代的镜子。无论是农夫对一个周而复始的农业生活的"铺陈其事",还是平民通过"以彼物比此物"对缠绵悱恻的男女之情的讴歌,它的赋、比、兴无不采撷自身边常见之物,习遇之事。《诗》中诚然不乏非"当代"题材的作品,如《大雅?生民》、《商颂?玄鸟》一类。但它们却往往淡去那本应笼罩诗中的神秘氛围,转而围绕农业,民族生存而铺叙,从而在格调上失去了初民那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天籁之音,并且人神、后裔祖宗之间,不可逾越。从人对神,后裔对祖宗毕恭毕敬之态投射出的,仍然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的需要和愿望。
与《诗经》相较,楚辞却走上离"经"叛道之途。由于楚辞的作者,身在楚国,当时的楚国,原始宗教一一巫教盛行。直到战国后期,楚国巫风依然很盛,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这就保存了大量的古老神话,丰富了作者的想像力,并且加上作者的历史、文化涵养,因而籍以表达其情怀、展示其主题的题材,并不完全取于"当代",而采撷自历史、神话。诗人"当代"的思维和道德判断乃通过洪荒时代的天神地祗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的种种表现,云蒸霞蔚一般地折射而出。题材与主题在时空上出现了巨大的反差。这种巨大的反差用一个专门的术语命名——悬隔。
存在着巨大悬隔的文学作品的主题与题材如上述呈二元状态,而不存在悬隔的文学作品主题与题材则呈一元状态。这种根本本质的差异,导致《诗经》、楚辞之间若干方面的迥异面貌。
从文艺学的角度判断,没有悬隔的文学作品在创作方法上,是写实的。如《诗经》
,
诚如其《风?七月》"所言皆农桑嫁穡之事,非身弓亲陇亩,久于其道,不能言之亲切有味也如是。"《七月》固然是这样,其他的诗也是如此。如《秦风?蒹葭》,其中汉水游女也好,蒹葭白露也罢,却是当时人们生活中习见习闻之物之人,主题与题材之间并未形成悬隔。乃至汉人解读《诗经》,认为"游女,汉神也",传说郑大夫交甫遇神女之事,主题与题材之间才产生了巨大的悬隔,从而使以所谓写实著称的《诗经》也涂抹了此扑朔迷离的色彩。而楚辞主题与题材之间的巨大悬隔反而决定其写作的非写实性。神话和历史传说纷纷被诗人驱遣至诗歌之中。诗人之意本在表现"当时"的情怀,但是诗中纷至沓来的神灵的祭祀,却真地起到了"五色令人目迷,五音令人耳聋"的作用。一时之间,读者似乎真的忘却了诗人所欲传达的"当代"主题,而迷离于深沉久远的历史追溯和五光十色的原始宗教氛围中。
从美学的角度判断,没有悬隔的文学作品,就审美的效果而言,给予审美者的感受是和诸、淳朴的。所谓"说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这种说法诚然是为
读《风》而发的,但移之以论全《诗经》,即良好形象地描绘出读者吟咏《诗经》时那种宁静、平和的审美心态。
而楚辞这主题和题材上的悬隔却于审美者以躁动的、不协和的审美心态。《离骚》中,诗人进入神游天际的幻想,设想自己在众神中择配偶,诏西皇,甚至令时光倒转,使自己得以从容地实现建功立业的怀抱,场面何等壮丽!但当时这样的题材而构造形成的光彩世界,由"忽临晚于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的此时此地的情愫打破时,主题与题材之间悬隔所造成的巨大碰撞带给审美者心灵的巨大震荡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心灵的痛苦在一些主题和题材并没有悬隔的作品,如《采薇》的结尾也能感受到。但这种痛苦只是由作品主题和题材造成的痛苦,属于伦理的痛苦,而主题与题材冲突造成的痛苦是悲剧,审美的痛苦,楚辞中其他作品也存在上述这种情况。如《天问》,为了表现诗人对"当代"的时俗激愤的主题,诗人向他之前的种种历史传说与众多君主发出了一连串激烈深沉的追诘和质问。仿佛倒并不是现存的,"当代"的楚国现实在使诗人愤怒和迷狂,而是过去的、即往的,已消逝的一切在让诗人痛不欲生。主题与题材的悬隔愈大,愈使审美者受到震撼人心的冲击。巨大的悬隔留下无限广袤的审美空间,使审美者可以多角度,多层次地审视作品。顺便指出,这种悬隔的空间的广狭,常常受制于审美者本身知识的厚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