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名人字号类型、规律解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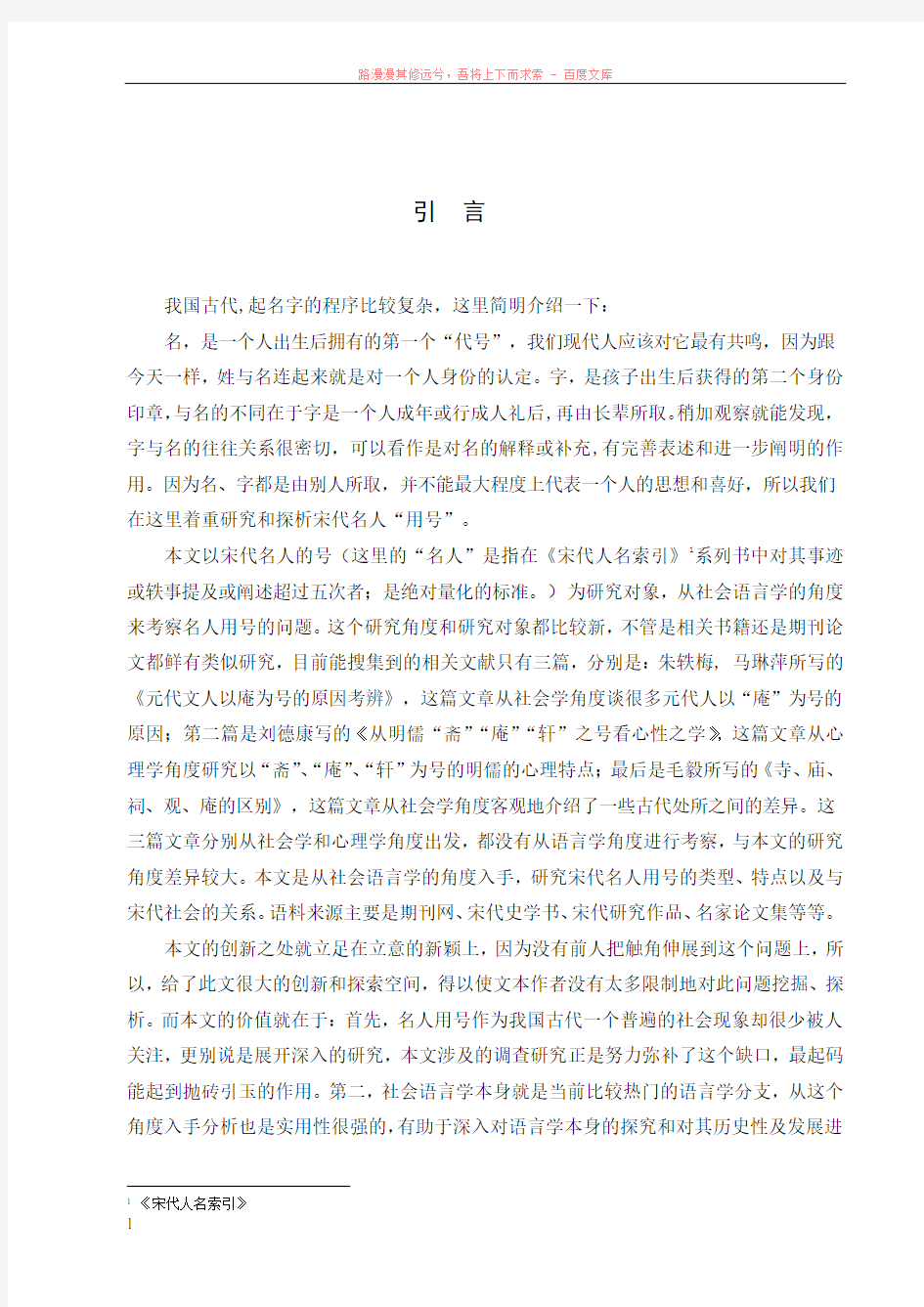

引言
我国古代,起名字的程序比较复杂,这里简明介绍一下:
名,是一个人出生后拥有的第一个“代号”,我们现代人应该对它最有共鸣,因为跟今天一样,姓与名连起来就是对一个人身份的认定。字,是孩子出生后获得的第二个身份印章,与名的不同在于字是一个人成年或行成人礼后,再由长辈所取。稍加观察就能发现,字与名的往往关系很密切,可以看作是对名的解释或补充,有完善表述和进一步阐明的作用。因为名、字都是由别人所取,并不能最大程度上代表一个人的思想和喜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着重研究和探析宋代名人“用号”。
本文以宋代名人的号(这里的“名人”是指在《宋代人名索引》1系列书中对其事迹或轶事提及或阐述超过五次者;是绝对量化的标准。)为研究对象,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考察名人用号的问题。这个研究角度和研究对象都比较新,不管是相关书籍还是期刊论文都鲜有类似研究,目前能搜集到的相关文献只有三篇,分别是:朱轶梅, 马琳萍所写的《元代文人以庵为号的原因考辨》,这篇文章从社会学角度谈很多元代人以“庵”为号的原因;第二篇是刘德康写的《从明儒“斋”“庵”“轩”之号看心性之学》,这篇文章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以“斋”、“庵”、“轩”为号的明儒的心理特点;最后是毛毅所写的《寺、庙、祠、观、庵的区别》,这篇文章从社会学角度客观地介绍了一些古代处所之间的差异。这三篇文章分别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出发,都没有从语言学角度进行考察,与本文的研究角度差异较大。本文是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入手,研究宋代名人用号的类型、特点以及与宋代社会的关系。语料来源主要是期刊网、宋代史学书、宋代研究作品、名家论文集等等。
本文的创新之处就立足在立意的新颖上,因为没有前人把触角伸展到这个问题上,所以,给了此文很大的创新和探索空间,得以使文本作者没有太多限制地对此问题挖掘、探析。而本文的价值就在于:首先,名人用号作为我国古代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却很少被人关注,更别说是展开深入的研究,本文涉及的调查研究正是努力弥补了这个缺口,最起码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第二,社会语言学本身就是当前比较热门的语言学分支,从这个角度入手分析也是实用性很强的,有助于深入对语言学本身的探究和对其历史性及发展进
1《宋代人名索引》
程的观察。
正如前面讲的,因为角度冷僻,所以在名人用号这个问题上的探究几乎是一个盲点,作者能够借鉴的研究成果是少之又少,所以,本文基本上是在没有任何参考的条件下另辟蹊径进行的:首先,根据网络和书籍集中查找了记载大量宋代名人的资料,再根据这些人名查对他们的用号,将这些号按一定标准分类后,再将这些类与宋代社会的各个方面的概况综合起来,分析它们的内在联系,并得出结论。虽然这样的研究方法显然缺乏深入性,也不可能达到很高的高度,但由于是前无古人的,所以也勉强成文,供其他研究者参考。
宋代名人用号的结构
(一)音节结构
现代汉语中,词语双音节化不仅已形成一种趋势,而且它也是词汇的特点之一。这主要是因为双音节词较之其他的音节结构更加简洁、响亮,而且朗朗上口。虽然相隔上千年,在遥远的宋代,双音节的名人用号竟也同今天一样占据多数,在我粗略统计的所有号中,双音节号占到了57%,确实远远超过三、四音节的号,在数量上居于主导地位。我想这种现象的原因应该与上述的类似。
在宋代名人使用的号中,三字节的号比起双音节的,数量要少得多,而且内容上看起来更随性、更贴近生活和口语化,比如:陈充,号中庸子;刘次庄,号戏鱼翁……
四音节号与二、三音节的相比,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它们虽然字数多,比较繁复,但表达却更直接有力,主人希望通过它们表达和传递的个人信仰、情绪、际遇等等通过短短四个字就非常清晰地传达出来了,比如:杨朴,号东里野民;刘宰,号漫塘病叟等不同音节结构的具体例子我们来看下表:
名号
音节数
名号名号名号
双音节戴溪岷隐董槐榘堂韩元吉南涧曹勋松隐罗适赤城刘德秀退轩刘颁公非郑獬云谷陈宗礼千峰陈括沱江郑燮安晚陈耆卿篔窗常挺东轩叶李亦愚陈显伯竹所徐履少初吴说练塘曾公亮乐正陈亮龙川陆游放翁陈文龙如心苏洵老泉方岳秋崖余安行月石张咏乖崖叶逵玉筠钱象祖止安赵卞清献冯澥雪崖苏庠眚翁许申化州孙林升肇殷喻汝砺三嵎洪天锡裕昆杨虞中老圃李献可松汀陈文龙如心方逢辰蛟峰敖陶孙臞翁汪元量水云吕徽之六松杨无咎易亭卢祖皋蒲江吴文英梦窗谢景初今是翁刘次庄戏鱼翁苏符白鹤翁王得臣凤台子
表二宋代名人用号音节结构表(三音节表)
名号
音节数
名号名号
三音节王得臣凤台子王古直黄松子陈充中庸子陈尧佐知余子
杜光庭东瀛子晁补之归来子陈搏扶摇子黄伯思云林子
表三
名号
音节数
名号名号
四音节周必大平园老叟戴复古石屏樵隐黄祖舜巩溪宫人杨朴东里野民史定之月湖老樵贺铸庆湖遗老黄庭坚山谷道人王庭卢溪真逸刘过龙洲道人苏辙颖滨遗老周密四水潜夫姜夔白石道人黄升花庵词客刘几玉华庵主刘宰漫塘病叟
(二)词语结构
如果说按音节结构划分是单纯从形式的角度出发,那么我们还可以再从内容+形式的角度入手——即按词语结构角度来划分名人用号,这样由浅入深、双管齐下当然更有助于我们客观、全面地研究宋代名人用号这个问题。
根据我所统计的各式各样的宋代名人用号,可以把它们分成这样三类:
专名;
专名+通名;
其他
“专名”是指那些没有固定形式和内容的用号,它们本身千姿百态、形形色色,但大部分号的来源到今天已无迹可寻,或者是考证起来非常困难,我们在这里无法深入追究,所以本文推测它们可能只是主人们根据个人的际遇、情感、理想、喜好等等而命。因为这种情况必然存在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对我们研究名人用号意义不大,所以本文也不对此做过多讨论。
“专名+通名”顾名思义是指专名带通名的用号形式,这样的号有自己非常明显和突出的规律,比如说以“庵”、“斋”、“居士”等为通名的号,这些号条理清楚、特点突出,但其中暗含的信息是什么、与宋代社会又有什么关系呢?这里我们埋下伏笔,留待下文详述。
“其他”,显然是指除了上述两种情况的其他类型的号,这样的号很少,这里也不赘
言了。具体例子详见下下表:
表二宋代名人用号“专名+通名”列表
名号
专名+通名
名号
专名+斋谢堂,号恕斋;聂子述, 号定斋;何溥,号潜斋;牟子才,号存斋;魏克愚, 号静斋;游似 ,号克斋;洪迈,号容斋;李塾,号约斋;包恢,号宏斋;李曾伯,号可斋;杜范, 号立斋;谢希孟,号晦斋;张舜民,号矴斋;袁甫,号蒙斋;林之奇,号拙斋;赵以夫,号虚斋;杨万里,号诚斋;罗愿,号存斋;郑性之,号毅斋;岳珂,号亦斋,赵葵,号庸斋;陈傅良,号止斋;余天锡,号畏斋;陈瓘,号了斋;洪咨夔,号平斋;马光祖, 号裕斋;岳珂, 号亦斋,陈与义,号简斋;李埴, 号悦斋……
专名+庵何耕,号怡庵;任希夷, 号斯庵;朱熹, 号晦庵;胡铨,号澹庵;赵范,号中庵;辅广,号潜庵;吴渊,号退庵;林安宅,号寓庵;叶革,号鼎庵;康与之, 号顺庵;罗点,号此庵;俞国宝, 号醒庵;赵葵,号信庵……
专名+叟张知白, 号清叟;李士彬,晚号石叟;韩琦,自号赣叟;
王履,号畸叟,司马光,晚号迂叟……
专名+山何基,号北山;萧泰来,号小山;胡安国,号青山;
郑起,号菊山;陆九渊,号象山;蒋捷, 号竹山;
王安石,号半山;谢文节,号叠山……
专名+溪王十朋,号梅溪;周敦颐, 号濂溪;字彦章,号浮溪;汪藻, 号龙溪;曹冠, 号双溪;余靖,号武溪;郑侨,号回溪;周敦颐 ,号濂溪;史达祖,号梅溪;王炎,号双溪;苏大璋,号双溪;刘辰翁,号须溪;严仁, 号樵溪……
专名+先生王次翁, 号两河先生;邵雍,号安乐先生;
苏迟,号涌泉先生;曾肇,号曲阜先生;
柳开,号东郊野夫、补亡先生;
罗从彦,号豫章先生;
陈襄,因居古灵,故号古灵先生……
专名+居士秦观,号淮海居士;周邦彦,号清真居士;
曾慥,号至游居士;辛弃疾,号稼轩居士;
赵孟坚,号彝斋居士;刘克庄,号后村居士;
王应麟,号深宁居士;李清照,号易安居士;
曾畿,号茶山居士;张元干,号芦川居士;
计有功,号灌园居士;范成大,号石湖居士;
尤袤,号遂初居士;张孝祥,号于湖居士;
朱淑真,号幽栖居士;刘克庄,号后村居士;
蔡伸,号友古居士;李弥逊,号筠溪居士、普现居士;
周紫芝,号竹坡居士;李邴,号龙龛居士;
郭祥正,号醉引居士、净空居士、漳南浪士等;
文同,号笑笑居士;张舜民,号浮休居士;
赵鼎,号得全居士;京镗,号松坡居士;
李壁,号雁湖居士;木待问,号抱经居士;
黄定,号巩溪居士;黄由,号磐野居士;
卫泾,号后乐居士、西园居士;李公麟,号龙眠居士;
赵令畤;号藏六居士;张方平,号乐全居士……
专名+老人章穆,号杏云老人;洪适, 号盘洲老人;
刘安世,号元城、读易老人;王庭珪,号泸溪老人;
周密,弁阳老人……
其他
冯道,其自号长乐老与李椿年的晚号逍遥公,这两个号异曲同工,它们形式上都是偏正词语,内容上也都是文人对自己的“简单定义”,这样的号显然没有深究的必要,这里简单带过。
一、宋代名人用号的特点
以上从不同角度归纳了宋代名人用号的类型,从这些号中我们已经能够勾勒出这一时期名人用号的一些特点:
(一)争当“居士”、类型不同
若能称之为用号特点,那一定是符合这种情况的号不仅数量多而且比较特别,有一定代表性,同时又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符合上述条件的宋代名人用号以“居士”很多这个现象当仁不让地成为了最突出的特点。
“居士”,它的词义总结如下:“居士”,梵语叫“迦罗越”。指代在家里修习佛法的人。在原始佛教时期,居士用来称呼“富有阶层中信奉佛而布施钱物于僧众者”。佛教传入我国后,“居士”虽然也用于称呼“积财而布施之士”,但一般情况下却是指代上述的第一种人,即取它的本来意义——“居俗而信佛之人”。中国古代,虽未出家但信佛习佛的“居士”很多,唐代白居易,号香山居士;宋代苏轼,号东坡居士;苏轼的朋友著名书法家、诗人黄庭坚,也是居士。清代居士彭绍升,于乾隆四十年编成的《居士传》共五十六卷,书中记录了中国自东汉以来各朝历代包括不少政治家和艺术家在内的著名居士传略,并着重记述他们有关佛教的言行。可见,“居士”的大量用于号也与佛道等宗教背景脱不了关系。
当然,以“居士”为号的其他朝代的人物也不是完全没有,比如,上文刚提到的、我们都熟悉的唐代白居易,号香山居士。但这种现象却在宋代达到鼎盛,不仅数量多,而且人物杂,换句话说,宋代最盛产“居士”。宋代名人中以“居士”命号的,以我粗略的统计已有几十位,占到了我所统计的近三百个号中的25%,而且他们当中包括了文人学者、佛道僧人、艺术大家、高官仕人等各种社会面貌、社会阶层的人……可想而知,若详细统计,“居士”的数目一定非常可观。这些人物遍布各个领域,他们的社会地位、生活际遇有很大的不同,但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以“居士”为号,这种现象不仅令人惊奇而且引人思考。这些“居士”构成了宋代名人用号的一道风景线,同时也是宋代名人用号的最显著特点。为何他们争当“居士”这点我们下文再谈,但对居士本身的探究却不能仅止于此,这里我们还要深入地分析一下“居士”。
从前文提到过的“专名+通名”的分析角度入手,居士可以分为三类:
1.“地理”居士
2.“情感”居士
3.“其他”居士
“地理”居士是指以各种地理事物作为专名的居士,溪流山川、村园斋轩……所有这些都算在内,比如说:秦观,号淮海居士;辛弃疾,号稼轩居士;南宋画家赵孟坚,号彝斋居士;南宋文学家刘克庄,号后村居士;李壁,号雁湖居士;南宋诗人曾畿,号茶山居士;南宋文学家计有功,号灌园居士;南宋词人张元干,号芦川居士;南宋诗人范成大,石号湖居士;周紫芝,南宋文学家,号竹坡居士;黄定,号龙屿,晚号巩溪居士;南宋词人张孝祥,号于湖居士;京镗,晚号松坡居士……
这些“居士”看似比较随意地以地理事物作为其前的专名,但我们在研究时却不能草率地认定它们是单纯的借用,因为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这些简单的地点往往寄托了名人们对其浓厚的感情、深切的眷恋或由衷的喜爱……比如说苏轼,其号为“东坡居士”,我们都知道这个号的来源是,谪居湖北黄冈时,城南门外有一个小山坡就东坡,所以称自己为“东坡居士”。显然,“东坡”看起来不是什么高雅的事物,但在先人心里却是任何其他的事物都无法代替的。由于条件所限,其他用号背后隐藏的深意和典故我们在这里就无法深入考证了,但我们希望就此问题的研究能在日后不断深入下去,开拓思路、精确结论。
“情感”居士与“地理”居士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前者的情感隐含,而后者的情感更外露。比如说:南宋女词人朱淑真,号幽栖居士;南宋学者王应麟,号深宁居士;蔡伸,号友古居士;木待问,号抱经居士;南宋女词人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南宋诗人尤袤,号遂初居士;南宋政治家、词人赵鼎,自号得全居士;张方平,号乐全居士;文同,号笑笑居士;北宋末、南宋初曾慥,号至游居士……
这样的号显然把主人的经历、情感、信念等等心理活动直接表露了,更直观也更直接。
“其他”居士就是指那些无法明确界定的“居士”。比如说:郭祥正,北宋诗人,自号谢公山人、醉引居士、净空居士、漳南浪士等;黄由,一号寅斋,自号磐野居士;赵令畤,北宋末南宋初词人。自号聊复翁,又号藏六居士。南宋大臣卫泾,号后乐居士、西园居士;北宋著名词人周邦彦,号清真居士;李邴,号龙龛居士;北宋文学家、画家张舜民,自号浮休居士,又号矴斋;史浩,北宋著名画家,号龙眠居士。号真隐居士;李弥逊,号筠西翁、筠溪居士、普现居士等……
这些“居士”很难一眼看出其来源或特点,所以归在“其他”里,但也不是说就没有深入研究它们的必要,只是我们篇幅有限,这里无法过多探讨。
以上三类,不论哪一种都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人的心境特征和真实体验,也都是我们日后研究宋代社会心理和社会状况可参考的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二)推崇宗教、佛道当先
虽然我们当今社会也存在形形色色的宗教派别,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但宗教在我国绝对不是社会的主要关注点或能够占据社会生活的主导地位,这与宗教在古代受重视和推崇的程度不可同日而语。宋代也不例外地使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影响广泛、难以忽略,这也构成了宋代名人用号的又一显著特点——推崇宗教。
这里的宗教完全可以具体到佛、道上,因为宋代的主要宗教就是佛道二教。
要论证这一点,我们可以先拿“斋”字来举例。“斋”是我们在上文提到的宋代名人用号的常见通名,有一定代表性。例子见下表:
表三以“斋”为号的宋代名人
以斋为号李塾,号约斋;包恢,号宏斋;
李曾伯,号可斋;杜范, 号立斋;谢希孟,号晦斋;张舜民,号矴斋;袁甫,号蒙斋;林之奇,号拙斋;赵以夫,号虚斋;杨万里,号诚斋;罗愿,号存斋;郑性之,号毅斋;岳珂,号亦斋
它的字义我们借助一些研究者的考证[1]:“纵观古今,‘斋’字的涵义多达十余种,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1、与宗教有关。一指僧道或信徒诵经释忏,祷祀求福等活动,亦是伊斯兰教五功之一。一指佛教语,比丘过午皆不许食,因以午前,午中之食为斋。后人引申以素食为斋。2、与精神活动有关。之古人在祭祀或举行其他典礼前清心寡欲,净身洁食,以示庄敬,引申为去除杂念,使心神纯一的心境。3、指家居的房屋。引申为书房的名称,也指学舍。”
“斋”字的三个义项都与佛教有关,可见它确实与宗教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再看“庵”字意义:1.小草屋,茅屋;2.佛寺,(多指尼姑住的)。两个义项其中之一与佛教有关;
[1]朱轶梅, 马琳萍:《元代文人以“斋”为号原因考辨》,衡水学院学报,2007年6月,第二期,38—39页
还有上文提到的居士,它的来源和日后的应用都与佛教关系密切。
另外还有些号与道教牵涉明显,比如:南宋文学家刘过,号龙洲道人;还有与苏轼并称“苏黄”的著名词人黄庭坚,其号山谷道人;
(三)文人有心、号中有情
从宏观和理性角度看,宋代的名人用号更多的是强调理性,不论是“居士”还是“先生”,抑或“老人”,外加“庵”、“斋”、“翁”、“子”、“山”、“溪”……所有的这些通名无一不是理性客观的事物,与个人情感和生活毫无关系,可是若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宋代名人用号就很有“感情”了,撇开现实性,这些号中浓厚的人文情怀也同样清晰可感。比如说,以“庵、斋”等为号的文人士大夫,我们后世的研究者可能会认为他们现实,因为这些号都是房屋居舍,没有情感,冰冷无趣,可是换个角度,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浪漫,或者说一种情怀。比如说:“庵”、“斋”都是栖身之所,那它们就与食之于生同等重要,所以,能以此为号的文人雅士一定是对生活乃至生命有思索、体悟,最起码是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和尊重的。
还有“山”“溪”,以这样的事物命号的人,我们就更不能认为他们没有感情了,相反,他们感情很丰富,并且与自然亲近,与生活和谐。
以“老人”为通名的名人用号也非常有意思,我们在这里简单分析一下。上文提到的以“老人”为号的例子包括章穆、洪适等,据记载,“老人”也确实大部分取于晚年,是他们的晚号,但我们不能因此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它们的主人单纯因为自己年岁已高才为自己命号“老人”,因为本文认为,“老人”其实指的不只是其真实的年龄,更多的是暗指一种垂垂老矣的心境和“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伤感。
拿宋代进士刘安世来说,他年轻时“从学于司马光,司马光教以诚心不欺妄……章惇用事,忌恶之,黜知南安军,贬少府少监,再贬新州别驾……”[1]可见,他的一生仕途不顺,那么其内心积压的苦闷体现在号上,为自己命号“老人”,暗呼自己一生烦闷低落的心境和颠簸坎坷的命运,就是我们非常能体会和理解的了。当然这些只是我们主观的分析,已无法得到历史的印证,但是我们相信:文人的自号与他们的作品一样,不可能是没有感情的。
简而言之,宋代名人用号中体现着他们的情绪、抒发着他们的情感、表达着他们的理想、寄寓了他们的人生……
这就是所谓“文人有心、号中有情”。
[1]百度
二、宋代名人用号与宋代社会
(一)宋代名人用号与宗教文化
宋代社会概况涵盖了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情况,包括经济、文化、思想、宗教、地域、风俗等等,而在这些不同的社会领域中,与名人用号关系最为密切、或者说对名人用号影响最大的是宋代宗教。正如本文在名人用号的特点分析中提到的,在宋代,与宗教有关的号极受推崇,这里我们就来分析一下此种现象的原因以及名人用号与宗教之间的关系。
首先,宗教对名人用号的影响。在宋代,宗教主要包括自汉朝传入中国的佛教以及生长于我国本土的道教两种。二者中,佛教虽为外来却更为活跃,是两宋历史上一直兴盛不衰的宗教,当然,这并不是说佛教在宋代的发展道路就始终平坦,陈振在《宋史》一书中提到:“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停废许多佛教寺院,并规定了相当严格的出家、考试及剃度制度,对佛教进行打击……”[1],而且,佛教在徽宗和真宗在位时也受到排挤,甚至还曾
“一直兴盛不衰”只是说在曾经任何排山倒海般的倒佛、遭受徽宗的大力灭佛活动的打击。
灭佛活动中它都没有被彻底打倒或衰弱下去,而是始终以顽强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影响力活跃在宋代的历史上。当然,如果仅仅是凭借传播较广和发展较快,显然还不足以成为佛教得到一些宋朝统治者的大力扶持并最终成为宋代主流宗教的理由,更重要的原因是它的思想学说对宋代统治者维护其统治和政权的作用巨大。佛教从汉代传入中国以后,它的经典著述的大量翻译和传播为其立足本土打下了必要的基础,再加上它与中国本土的道教和儒家思想的互相渗透和糅合,就更加逐渐地地出离了本来的面貌而越发适应本土的需求,以此慢慢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思想宗派,同时也成为了统治者加强统治的有力工具和思想武器。综上,佛教能够对宋代名人用号产生直接和广泛的影响就不足为奇了。
另一方面,名人用号又是如何反作用于宗教的呢?那就是如实地反映并通过把与宗教有关的很多事物当做号来响应佛教的广泛的影响力,上面的很多例子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二)宋代名人用号与儒学思想
我们都知道,儒学是由孔子创立于春秋时期的学术思想,它所强调的仁义礼智信等思想观念长久以来深入人心,我国古代把儒学当做立国和治国之学的朝代也不占少数,汉代的董仲舒把儒学加以改善,使其更加适应当时社会和统治的需要,为统治者和其巩固政权[1]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服务,也使儒学思想达到了一个传播和发展的高峰,使其地位一时无二。而到了宋代,由于社会政治结构、经济文化、国家发展以及名族矛盾等各方面情况的变化,儒学也不可能再以一成不变的形式和内容服务于当前社会和统治了,它不得不使自己固守、沉闷的思想变化和改善、蜕变和成长。就此我们要探讨的就是在宋代社会需要下应运而生的新儒学或者说宋学了。
“新儒学以儒家为宗,吸收儒、道诸家思想的有益成分,逐步形成新的学术体系,在内容与形式上都表现出不同于前代的鲜明特征。”[1]
“赵宋王朝虽然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割据战争的局面,但由于过去社会分裂和混乱,造成伦常破坏、道德沦丧,人们不仅无法遵循,而且削弱作为维系社会安定的道德准则。这就急需借重于儒者来重建纲常,以维护统治秩序。”
“从总体上说,新儒学研究的主题,自范仲淹研究《易》学,开创宋学时开始,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是:探求自然界于人类社会变化的法则,人与自然的关系;以自然比附人类社会,用以论证伦理纲常;不违背“天命”,但强调“人事”之重要,为赵宋王朝统治提供理论依据。”[2]
“‘内圣外王’”四个字很形象地概括了宋学家们既重内求,又贵实用,特别讲求的主题——力求实践的最高理想境界。宋学所谓内求,既是指内心修养的追求,又是指对经书内在思想的体认,尤重于那些经书已经提及而尚未展开讨论的命题。(两宋文化史 477页)
本文讨论的宋代名人用号问题在宋代新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受也到了很大的、不可忽略的影响,我们在庵、斋等通名前的专名上就能看出来:恕、定、潜、存、克、约、毅、了、容、简、悦;晦、顺、退、醒、信……
一种随性又自省的生活态度,这些可以从这些号的专名上看出来:可见,这些“庵”“斋”也许不是富丽堂皇的华室邃宇,但却体现着主人的高洁品格,可谓“与乾坤清气相通”。从这些字上,我们仿佛能够想象他们在这些“斋、庵”中做学问时所追求的心神凝聚、清心寡欲、淡薄宁静,想象着何谓:“湛然虚明,平旦之气略无所挠,绿阴清昼,熏风徐来,而山林宁寂,天地自阔,日月自长。邵子所谓心静方能知白日,眼明始会识青天,于斯可验”[3]。
(三)宋代名人用号与地理情况
[1]杨渭生《两宋文化史》2008年版476页
[2] 杨渭生《两宋文化史》2008年版476页
[3]刘康德:《从明儒“斋”“庵”“轩”之号看心性之学》,《社会科学》,1997年第六期,50页
宋代名人用号是很有特点的,上面已经提过了。在那些显而易见的特点之外,这里我们还要关注一下这些用号与另一个社会方面隐含的联系,那就是地理,或者说地理情况。我们仔细观察宋代名人用号就会发现,很多号都与地名或一些地理方面的事物有关。这一点在介绍“居士”的类型时已有提及,这里进一步阐释一下,不求深入,但求言之成理,为其他研究者提供思路。例子如下:
崔与之,号菊坡;龚原,号武陵;张澄,号澹岩;汤汉,号东涧;韩元吉,号南涧;张咏,自号乖崖;陈括,号沱江;卢祖皋, 号蒲江;吴说,号练塘;冯澥,号雪崖;王庭,自号卢溪真逸;黄祖舜 ,晚号巩溪宫人;黄庭坚,自号山谷道人;贺铸,号庆湖遗老;刘宰,号漫塘病叟;李壁,号雁湖居士;陈慥,号龙丘居士;王安石,号半山居士;苏轼,号东坡居士;叶梦得,号石林居士;曾畿,号茶山居士;李壁,号雁湖居士;周紫芝,号竹坡居士;郑汝谐,号东谷居士……
为什么这么多宋代名人用号都与地理事物有关呢?程民生先生著的《宋代地域文化》一书就详细地介绍了地域差异和地域文化给宋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的影响,无论从经济到文化、从宗教到儒学,还是从风俗到人口,地域差异都对其影响巨大而且明显,甚至,正如程民生先生说的:“地域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地域独特性”,“世代相袭的各地风俗习惯,使人们对生长地的一切都感到亲切合理,而对异地的东西在新奇之处,总有不习惯乃至排斥。”[1]
虽然地域问题很复杂,不是一篇文章,甚至一本书就能说清道尽的,但显然名人用号问题也深受地域性影响。那么多的地名、地理事物对以其命号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无法在这里详细考证和说明,但这里我们只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关联就够了,起码已经将它们的密切联系呈于纸上,并能够使其他的研究者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在日后的探究中深入下去。
(四)宋代名人用号与统治政权
如果说佛道与儒家学说对宋代名人用号的影响是直接的,那么宋代统治者、统治政权对名人用号的影响就是间接的,但其力量很大。
在宋代,佛道二教的融合以及二者与儒家学说的相互借鉴和吸收是宋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和政权稳定极力推动的社会潮流,并得到了众多佛道大师与儒家学者的广泛响应。
据周宝珠、陈振合著的《简明宋史》中记载,道教在宋代也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赵宋王朝对道教极为提倡,尤以太宗、真宗、徽宗三朝为盛……真宗更是道教的狂热鼓吹者。
[1]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2005年版, 44页
从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起,他演出了一连串的“天书”闹剧,又虚构一个赵姓祖先赵玄朗,奉为道教的天神,尊为‘太上混元皇帝’,这当然都是荒诞无稽的事。但在整理道藏方面,却又成就。”
以上的信息都证明了宋代统治政权对包括佛道在内的宗教发展走向及社会思想的发展趋势等方面都有主导作用,目的当然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但这却无形中对与它没有直接联系的名人用号产生了间接的、却不常被发现的巨大影响。上文已提到过,宋代名人对与宗教有关的用号很推崇,其直接原因当然是佛道在当时社会的地位和作用,但其实统治政权才是这种现象背后强大的推动力……
结语
这篇文章从宋代名人用号入手,想通过分析一些有特点和规律的名人用号、再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比如宗教、思想流派等方面的情况来综合分析宋代名人用号的类型、特点和这些特点产生的原因等,这种立意应该比较少见,而我认为名人用号这个问题虽不常被关注,但这个角度是值得留意一下的,比如文章中提到的“庵”“斋”“子”“居士”等用号,它们的广泛使用并不是偶然的,那么多人的相同做法更不是巧合,而是隐含一些信息的,捕捉了这些信息后,我们也发现它们确实是当时社会很多方面发展变化的产物,这样,文章的目的就达到了,就是把名人用号同社会大背景联系起来,找出它们的关联,由此,让人们能够意识到宋代名人用号并不是无规律可循的,或者说,很多时候并不是那么随意的,那么,其他时代的名人用号有没有什么规律或特点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来研究和思考这个问题,有越来越多的信息能从名人字号这个问题中渗透出来,用于深化或拓宽对一些历史和名人研究的思路……
参考文献
[1]俞如云:《宋史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周宝珠、陈振著《简明宋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朱瑞熙著《宋史研究论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包伟民、吴铮强著《宋朝简史》,福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虞云国著《细说宋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6]徐洪兴、姚荣涛著《大宋王朝》,长春出版社,2007年版
[7]吴泰著《宋朝史话》,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7年版
[8]邓广铭著《宋史十讲》,中华书局,2008年版
[9]陈振著《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0]杨渭生等著《两宋文化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1]刘康德,《从明儒_斋_庵_轩_之号看心性之学》,《社会科学》1996年,第六期
[12]毛毅,《寺、庙、、祠、观、庵的区别》,《四川统一战线》2009年1月
[13]朱轶梅, 马琳萍,《元代文人以_斋_为号原因考辨》, 衡水学院学报,2007年6月,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