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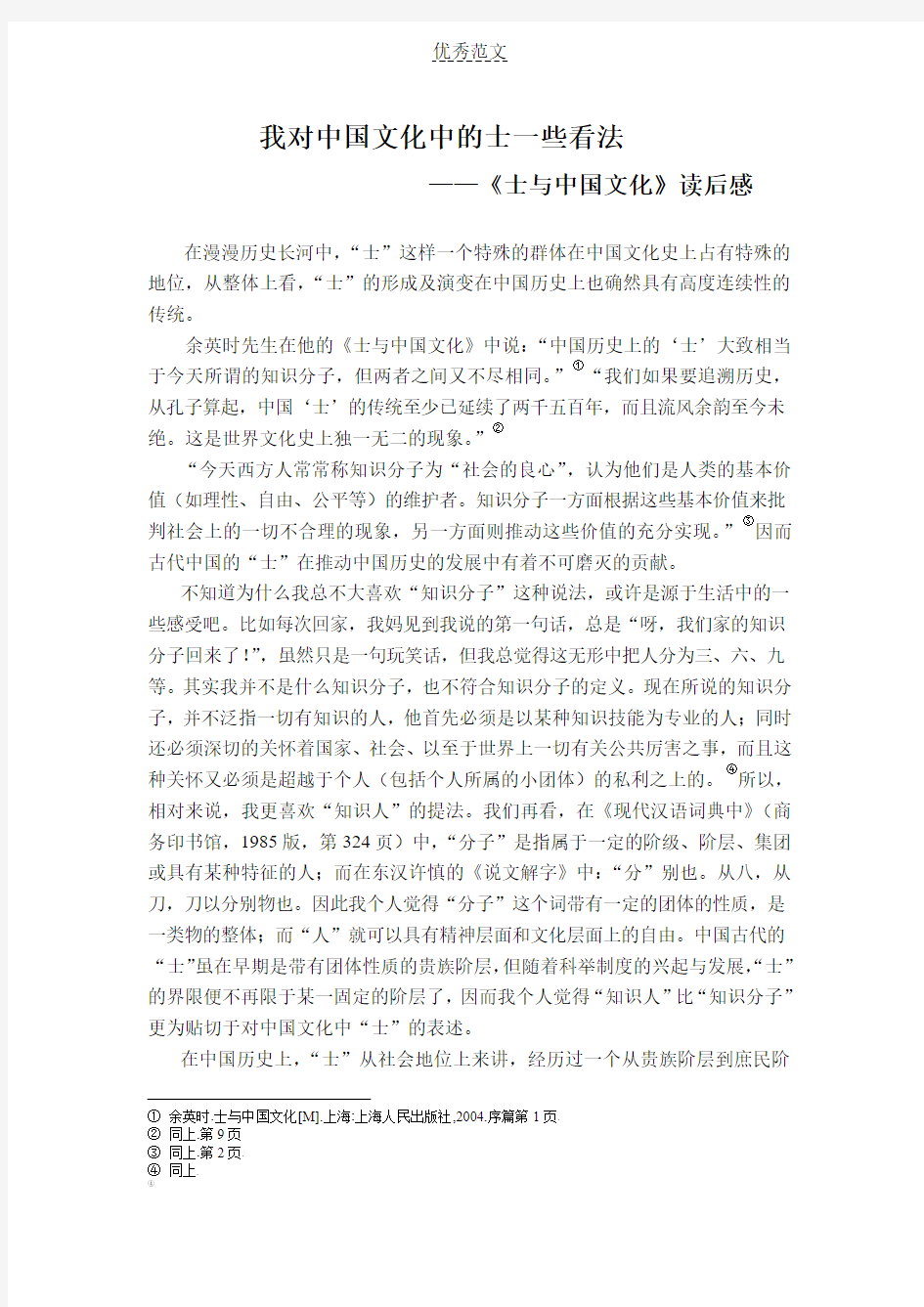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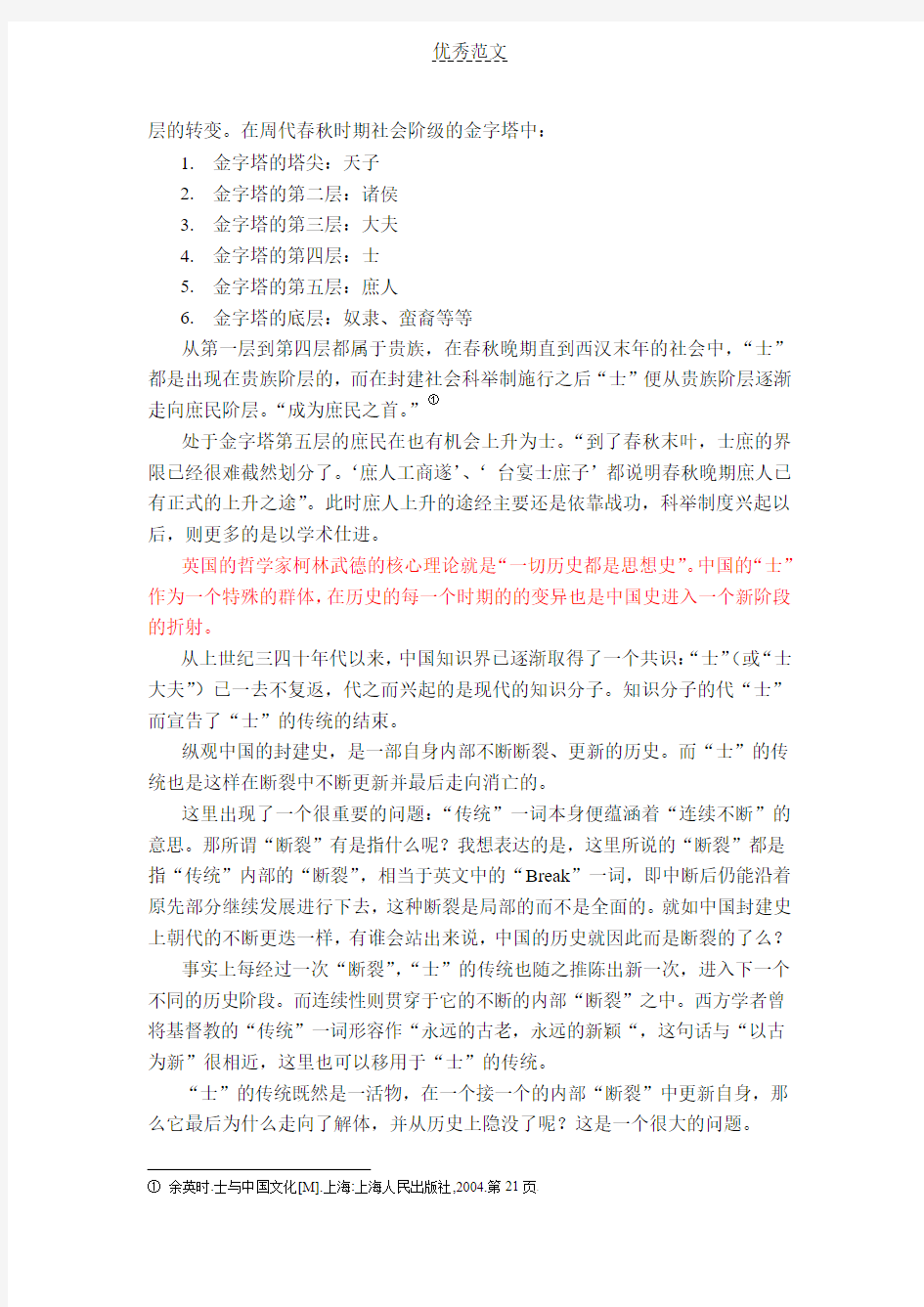
我对中国文化中的士一些看法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士”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从整体上看,“士”的形成及演变在中国历史上也确然具有高度连续性的传统。
余英时先生在他的《士与中国文化》中说:“中国历史上的‘士’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但两者之间又不尽相同。”①“我们如果要追溯历史,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而且流风余韵至今未绝。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②
“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③因而古代中国的“士”在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不大喜欢“知识分子”这种说法,或许是源于生活中的一些感受吧。比如每次回家,我妈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总是“呀,我们家的知识分子回来了!”,虽然只是一句玩笑话,但我总觉得这无形中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其实我并不是什么知识分子,也不符合知识分子的定义。现在所说的知识分子,并不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他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同时还必须深切的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于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厉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④所以,相对来说,我更喜欢“知识人”的提法。我们再看,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商务印书馆,1985版,第324页)中,“分子”是指属于一定的阶级、阶层、集团或具有某种特征的人;而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分”别也。从八,从刀,刀以分别物也。因此我个人觉得“分子”这个词带有一定的团体的性质,是一类物的整体;而“人”就可以具有精神层面和文化层面上的自由。中国古代的“士”虽在早期是带有团体性质的贵族阶层,但随着科举制度的兴起与发展,“士”的界限便不再限于某一固定的阶层了,因而我个人觉得“知识人”比“知识分子”更为贴切于对中国文化中“士”的表述。
在中国历史上,“士”从社会地位上来讲,经历过一个从贵族阶层到庶民阶
①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序篇第1页.
②同上.第9页
③同上.第2页.
④同上.
④
层的转变。在周代春秋时期社会阶级的金字塔中:
1.金字塔的塔尖:天子
2.金字塔的第二层:诸侯
3.金字塔的第三层:大夫
4.金字塔的第四层:士
5.金字塔的第五层:庶人
6.金字塔的底层:奴隶、蛮裔等等
从第一层到第四层都属于贵族,在春秋晚期直到西汉末年的社会中,“士”都是出现在贵族阶层的,而在封建社会科举制施行之后“士”便从贵族阶层逐渐走向庶民阶层。“成为庶民之首。”①
处于金字塔第五层的庶民在也有机会上升为士。“到了春秋末叶,士庶的界限已经很难截然划分了。‘庶人工商遂’、‘台宴士庶子’都说明春秋晚期庶人已有正式的上升之途”。此时庶人上升的途经主要还是依靠战功,科举制度兴起以后,则更多的是以学术仕进。
英国的哲学家柯林武德的核心理论就是“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中国的“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历史的每一个时期的的变异也是中国史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折射。
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已逐渐取得了一个共识:“士”(或“士大夫”)已一去不复返,代之而兴起的是现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代“士”而宣告了“士”的传统的结束。
纵观中国的封建史,是一部自身内部不断断裂、更新的历史。而“士”的传统也是这样在断裂中不断更新并最后走向消亡的。
这里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传统”一词本身便蕴涵着“连续不断”的意思。那所谓“断裂”有是指什么呢?我想表达的是,这里所说的“断裂”都是指“传统”内部的“断裂”,相当于英文中的“Break”一词,即中断后仍能沿着原先部分继续发展进行下去,这种断裂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面的。就如中国封建史上朝代的不断更迭一样,有谁会站出来说,中国的历史就因此而是断裂的了么?
事实上每经过一次“断裂”,“士”的传统也随之推陈出新一次,进入下一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而连续性则贯穿于它的不断的内部“断裂”之中。西方学者曾将基督教的“传统”一词形容作“永远的古老,永远的新颖“,这句话与“以古为新”很相近,这里也可以移用于“士”的传统。
“士”的传统既然是一活物,在一个接一个的内部“断裂”中更新自身,那么它最后为什么走向了解体,并从历史上隐没了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①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21页.
我认为,这是缘于一切的活动都需要遵循规则,一旦规则不能再约束活动行为,那么之前一直延续的就会不复存在。
“士至于道”,这是孔子最早为“士”所定下的规定。所以“士“在中国史初次出现的时候便有了参与“治天下”的要求。这个要求是普遍的,并不局限于儒家。司马谈就告诉我们“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①从先秦以来“士“就不断的有参政的要求,在汉代,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等人的“独尊儒术”的提议之后,不但郡县举孝廉改以“士”为对象,太学中博士的弟子更成为入仕的重要途径。从此汉代官吏由“士”出身便制度化了。
从隋唐到明清一千年间,“士”在文化与政治方面所占据的中心位置是和科举制度分不开的。通过科举考试,“士”直接进入了权利的大门,他们的仕宦前程已经有了制度的保障。但这也决定了中国“士”的悲哀。“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读书中举成为“士”唯一晋身仕途的途径,一辈子在科举教育中度过,有多少人能跨过那道龙门,飞黄腾达呢?大多是像孔乙己一样,连半个秀才都捞不到。孔乙己的形象代表着许多在科举考试中不能中举的“士”的形象,为一个飘渺的目标而虚度一生。可悲可叹!
“士”的传统虽然在现代结构中消失了,但“士”的幽灵却仍然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的缠绕在现代中国知识人的身上。“五四”时期,知识人追求“民主”与“科学”,单从他们在行为模式上来看,仍摆脱不了“士以天下为己任”的余韵。有一位西方思想家在二十世纪末曾对中国的知识人这种精神感到惊异。他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把许多现代价值的实现,包括公平、民主、法治等,看成是他们独有的责任,在西方社会中,这些价值的追求是大家的事,知识分子并不比别人应该承担更大责任。他的这种惊异,在我们看来却很是平常,因为知识分子的这种思维模式是受到了“士”文化的长期熏染,摆脱不了“士”的阴影。
中国文化中的“士”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我也不再做更详细的论述,就这样浅谈即止吧,即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已。
①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7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