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罪人”不“千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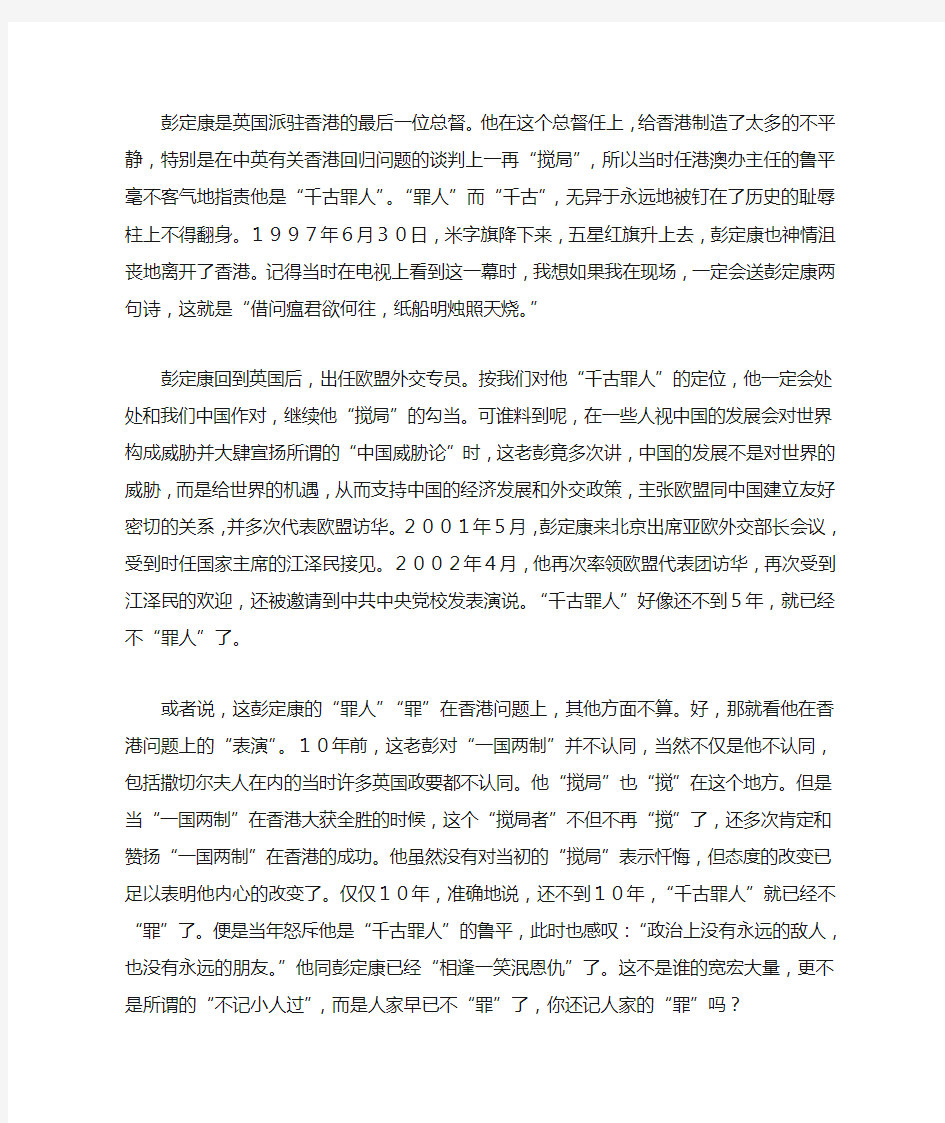

彭定康是英国派驻香港的最后一位总督。他在这个总督任上,给香港制造了太多的不平静,特别是在中英有关香港回归问题的谈判上一再“搅局”,所以当时任港澳办主任的鲁平毫不客气地指责他是“千古罪人”。“罪人”而“千古”,无异于永远地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不得翻身。1997年6月30日,米字旗降下来,五星红旗升上去,彭定康也神情沮丧地离开了香港。记得当时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幕时,我想如果我在现场,一定会送彭定康两句诗,这就是“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彭定康回到英国后,出任欧盟外交专员。按我们对他“千古罪人”的定位,他一定会处处和我们中国作对,继续他“搅局”的勾当。可谁料到呢,在一些人视中国的发展会对世界构成威胁并大肆宣扬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时,这老彭竟多次讲,中国的发展不是对世界的威胁,而是给世界的机遇,从而支持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外交政策,主张欧盟同中国建立友好密切的关系,并多次代表欧盟访华。2001年5月,彭定康来北京出席亚欧外交部长会议,受到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接见。2002年4月,他再次率领欧盟代表团访华,再次受到江泽民的欢迎,还被邀请到中共中央党校发表演说。“千古罪人”好像还不到5年,就已经不“罪人”了。
或者说,这彭定康的“罪人”“罪”在香港问题上,其他方面不算。好,那就看他在香港问题上的“表演”。10年前,这老彭对“一国两制”并不认同,当然不仅是他不认同,包括撒切尔夫人在内的当时许多英国政要都不认同。他“搅局”也“搅”在这个地方。但是当“一国两制”在香港大获全胜的时候,这个“搅局者”不但不再“搅”了,还多次肯定和赞扬“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他虽然没有对当初的“搅局”表示忏悔,但态度的改变已足以表明他内心的改变了。仅仅10年,准确地说,还不到10年,“千古罪人”就已经不“罪”了。便是当年怒斥他是“千古罪人”的鲁平,此时也感叹:“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他同彭定康已经“相逢一笑泯恩仇”了。这不是谁的宽宏大量,更不是所谓的“不记小人过”,而是人家早已不“罪”了,你还记人家的“罪”吗?
当然,谁要认为这是彭定康的洗面革新、回头是岸,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并非洗面革新、回头是岸,他还是原来的他。他当初“搅局”,是出于维护英国的利益;他主张欧盟同中国建立密切的经贸关系,则是出于维护欧盟的利益;他肯定“一国两制”的成功,一则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二则这并不损害英国的利益。他绝不会出于维护咱们中国的利益才有了后来的表现,只不过是他维护的英国利益、欧盟利益同咱们中国的利益并不矛盾,而触犯中国的利益也会危及他们自身的利益罢了。咱们有一句古话“各为其主”,那是在君王时代,君王是臣下的主人,臣下不过是君王的奴仆。分属其主的臣下互相谈判时都“各为其主”,而且还要做到“不辱君命”。现在当然不再是“各为其主”了,乃是“各为其国”。鲁平是这样,彭定康也是这样。彭定康无论是当初的“搅局”,还是后来的“和局”,都不过是为“其国”。
“千古罪人”是文学语言,科学意义上、历史意义上的“千古罪人”很少。汪精卫算一个,他当了不齿于中国人的汉奸。袁世凯也算一个,他在每一个历史关头都站在历史前进的对立面。但有些人罪孽深重,永远也难以翻案,却未必当得起“千古罪人”,就像有些人想“遗臭万年”,可能一年、几年后人们就记不得他了。他想“万年”,恐怕连十年也不可得。而有些当得起“千古罪人”的,又未必就是“千古”。那个北洋军阀吴佩孚,曾残酷镇压武汉工人大罢工,杀害工人领袖,可谓“千古罪人”。可他晚年在北京,坚决拒绝日本人的邀请去当汉奸,又表现了中国人铮铮的民族气节。李鸿章也曾被称为“千古罪人”,他在“中堂”的任上,代表清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但谁又能不承认,他是清朝末年朝廷里最有作为的一个大臣呢!他签订那些条约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不幸。便是蒋介石,至少是反对台湾独立的吧。那些“台独”分子恨他,也主要恨在这个地方。
有句话说得好:世界有多复杂,我们人就有多复杂。世界在变化中,人也在变化中。一
成不变的,有,少。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同英国、法国、美国的关系紧张,互相视为敌人;而苏联同德国的关系则相对友好密切得多。双方不但签订友好条约,还有各获其利的处置邻国的秘密协定。这也正是德国突然袭击苏联时,苏联疏于防范的原因。但后来,苏联却同英、法、美结成了反德的联盟,此前谁能想得到呢?可见,“千古罪人”,当其还不能盖棺论定的时候,就不能轻易地给他“千古”。即使当时出于义愤给他“千古”了,也不能把这“千古”的大门永远紧紧地关上,至少应当留一个缝,说不定什么时候或在什么问题上,他就会从这“千古”的大门里出来呢。这不是宽宏,而是明智,是对事理的洞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