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权力观_由_规训与惩罚_说起_余晓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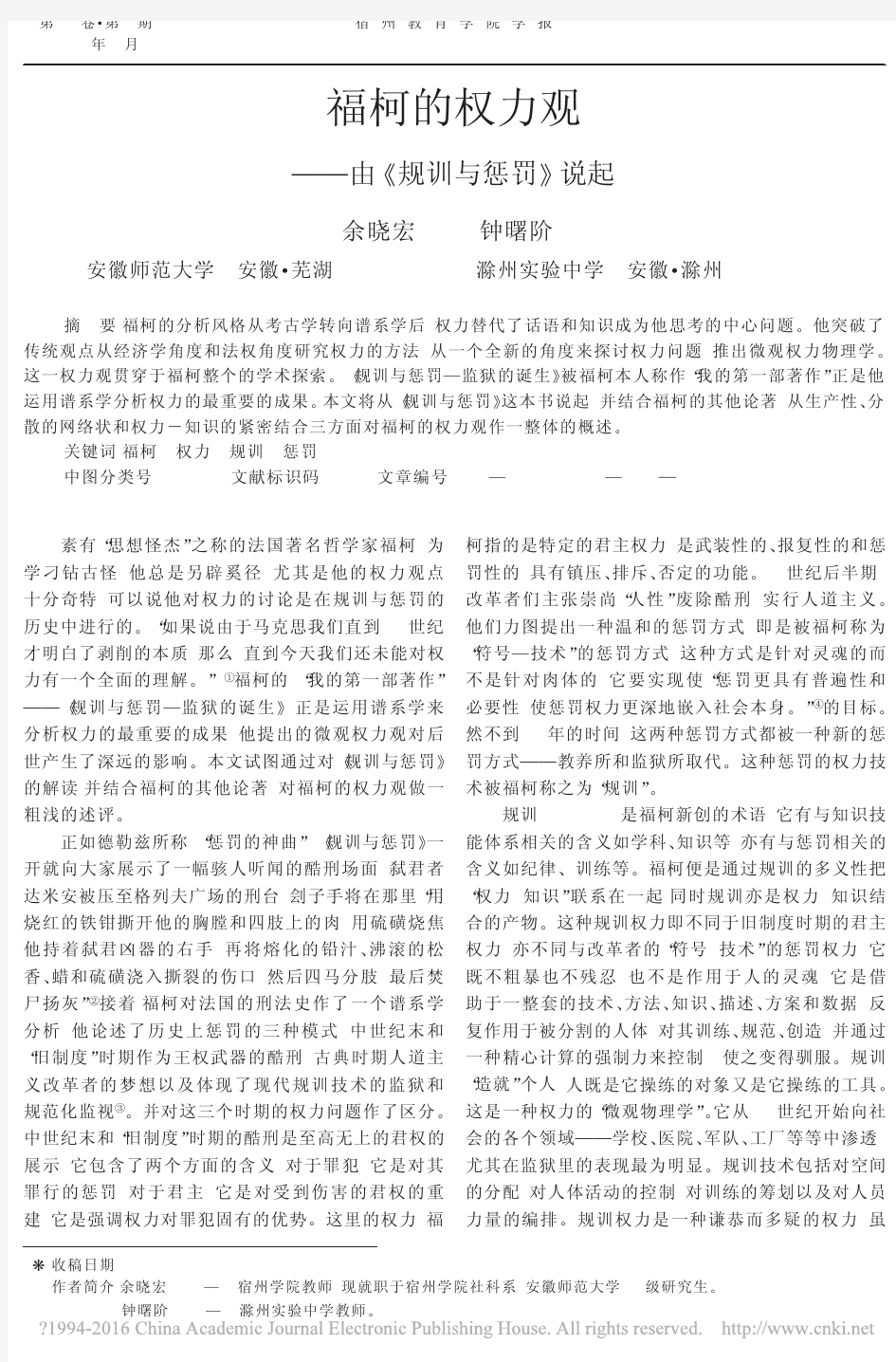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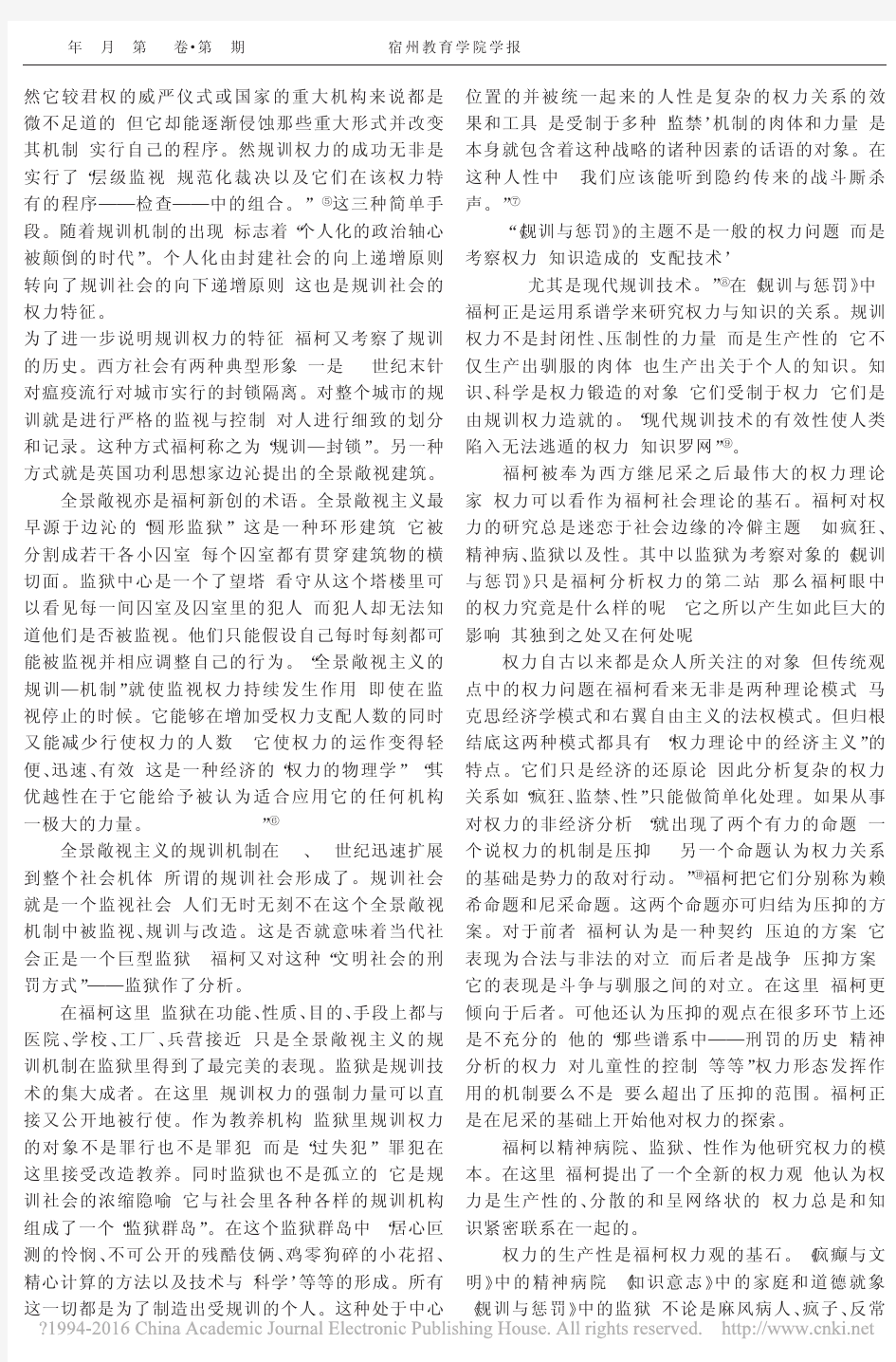
社会批判理论的范式演进:从福柯、哈贝马斯到霍耐特的论文
社会批判理论的范式演进:从福柯、哈贝马斯到霍耐特的论文 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社会批判理论在工具理性的意义上理解“理性”,强调“实践的意图”、人对于自然的绝对支配地位,忽视了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中人的交往行动方式和自由的限制,从而囿于意识哲学框架而不能自拔。福柯的权力理论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均以法兰克福学派为渊源,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为己任,致力于对早期社会批判理论二难困境的系统解决。其中,福柯主张权力的策略模式,在永不间断的策略斗争行动过程中实现个体的社会化。哈贝马斯则主张主体间无支配的自由交往,把主体间相互理解置于交往行动理论的核心位置。但是,福柯偏离了规范共识和策略性互动,哈贝马斯也陷入了系统与生活世界二元结构的困境。这两种理论范式均不能成为新时期社会分析与时代诊断的规范性基础。霍耐特着力在后形而上学的哲学视野中继续为社会批判理论重构规范性基础。他的承认理论揭示了社会行动的“斗争和理解”的双重维度,为新时期社会斗争的兴起和主体间自由交往提供了规范性解释框架,从而实现了批判理论的“承认范式转向”。 一、福柯的权力理论与“非理性”的斗争 福柯的知识符号学分析一直阻碍着他对“个体起源”、“个体如何行动”等问题的清晰认识,致使他在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如何得到合理解释的问题上,陷入了自我矛盾的假设之中。只有在福柯试图运用“权力的策略斗争模式”系统分析社会事件和社会行动、并为时代作出诊断的意义上,他的权力理论才可称为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 福柯借用尼采的“权力关系多样性”理论,认为权力无处不在,是一种支配性、生产性的力量,如一张巨网笼罩在整个社会之上,一切社会关系均可从权力角度得到解释说明。但福柯反对将权力视为先于其实际表现和效应、具有恒常齐一性质的某物,反对以某一普适性权力概念作为出发点一劳永逸地解答所有现实问题的企图。他主张权力“去中心化”,从权力结构内部多元异质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考察权力,从而将权力微观化、复数化。正是在权力“去中心化”的意义上,他强调用斗争模式解释权力关系的动态性和多样性,认为一切个体(而非集体)均为权力所生产,为权力而斗争;言下之意是,权力主体并不是某一个或一类人,每个人都是权力的主体。 通常认为,权力一般可以作为契约规定或强力获取的拥有物(honneth, )。其中,前者源自人民权力的让渡,后者源于力量的对比,强者为王。福柯则反对这两种观点。他主张权力的策略模式,认为权力不应该作为一个固定的所有物和一个社会群体中某一个体的永久性特征,而应作为主体间策略冲突“敞开的”的产物。因此,社会权力的获取与维持发生在社会行动者之间不断的斗争当中,而不是发生在法律权力或强迫的单面行使中。 那么,在社会主体之间策略冲突的持续过程中,权力斗争的实现机制如何展现?福柯的“微观权力学”用“力量关系”来思考权力,把社会机体层次化、结构化、权力化,在微观层面考察渗透着权力效应的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而在宏观上把握社会中各种权力关系(结构)涌现和演变的机制,以及这一机制对人的压抑。(薛伟江,第17页)他视社会主体之间的策略行动为社会权力形成和实践体现的不间断过程。权力根植于长期不断的战斗、斗争,权力关系就是斗争关系,斗争是事物(人)的存在状态。一切都在权力斗争当中生长、灭亡、再生长、再灭亡,和平只是斗争的派生物。因此,权力总是许多具体个体间一种暂时的和不断重复的冲突形式。(honneth,)每个社会都处在持续不断的斗争状态之中,均是独立的个体与集体行动者之间策略关系的连结体。 可见,福柯利用权力概念是要揭示社会发展的“自组织”动力学,把社会首先理解为是一个策略斗争行动的永不间断过程。早期社会批判理论(如阿多诺、霍克海默等)跳过社会行动的现象,在一般意义上将社会结构静态地理解为自然控制活动的凝固形式。福柯的“权力微观物理学”则在动态上超越了早期社会批判理论,“是对阿多诺、霍克海默用历史哲学分析
福柯 疯癫与文明 解读
福柯疯癫与文明解读 福柯是后现代思想的领军人物,在当代西方,他以“理性批判者”著称。在《疯癫与文明》中,他将研究对象集中指向疯癫、疾病、犯罪和性等“边缘”领域,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对疯癫中富有想象力和诗意的部分进行了阐释和颂扬,而对所谓的理性精神中隐秘的残忍却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在此书中,福柯通过对理性时代疯癫史的考察,批判了西方社会长期以来以理性名义对非理性(疯癫)的禁闭。他向我们完整的介绍了整个理性时代的疯癫史。照福柯看来,西方社会对疯癫的态度分为三个阶段:1、文艺复兴时期的自觉;2、古典时代的大禁闭;3、现代社会的精神病理学说。 一、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 福柯选择了从文艺复兴时期(15世纪到17世纪)开始。该时期堪称疯癫者的“黄金时代”,他们没有被作为异质分子受到打压,他们表现出的“病症”也因为被看作是一种跟梦幻和想象力紧密相关的现象而成为艺术家的描绘对象。即使在一段时间里疯癫者受到排斥和驱逐,他们也是乘着德国诗人布兰特笔下的“愚人船”过着一种极富浪漫色彩的流放生活。 在这个时期,疯癫是作为一种美学现象或日常现象出现的。“人与疯癫的争执是一种戏剧性辩论,其中人所面对的是这个世界的各种神秘力量;疯癫体验被各种意象笼罩着:人类的原始堕落和上帝的意志,兽性及其各种变形,以及知识中的一切神奇秘密”。在这一时期,用福柯的话说就是“疯癫在各个方面都使人着迷”。首先,疯癫之所以有魅力,在于它就是知识。当有理性、有智慧的人仅仅感受到片断的,从而越发令人气馁的各种知识形象时,天真的愚人却拥有完整无缺的知识领域,疯癫是智慧之身。这在当时的民间传说、滑稽戏中以及各种戏剧人物,如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和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都有充分的表现,疯癫是前古典文学的悲喜剧结构中的重要把戏。在这些戏剧中,疯癫者往往以病态来捉弄人,而后用病态的语言道出事物真相,道出人能知觉的“有关自身的一切真相”。 但福柯同时又认为,“如果说知识在疯癫中占有重要位置,那么其原因不在于疯癫能够控制知识的奥秘;相反,疯癫是对某种杂乱无用的科学的惩罚。如果说疯癫是知识的真理,那么其原因在于知识是荒谬的,知识不去致力于经验这本大书,而是陷于旧纸堆和无益争论的迷津中。正是由于虚假的学问太多了,学问才变成了疯癫”。从这个时期长期流行的讽刺主题也可以看出,疯癫在这里是对知识及其盲目自大的一种喜剧式惩罚。疯癫所涉及的语气说是现实世界,不如说是人和人所能感受到的关于自身的所谓真理,疯癫也由此进入了一个完全的道德领域。在15世纪的文学和哲学领域,疯癫经验一般都用道德讽喻来表现的,并以一种持久的形态保存在文学文本之中,不论是浪漫化的疯癫,狂妄自大的疯癫,正义惩罚的疯癫,还是绝望情欲的疯癫,似乎都是在谴责人们的不断行为。 在文艺复兴时期,疯癫的另一吸引人之处是它统治着世上一切轻松愉快乃至轻浮的事情。正是疯癫、愚蠢使人变得“好动而快乐”。“疯癫是社会画面上一个司空见惯的身影。从旧式的疯人团体中,从他们的节日、聚会和交谈中,人们领略到一种新鲜活拨的愉悦”。总之,从任何意义上讲,这个世界在文艺复兴时期对疯癫是特别友善的,“疯癫在人世中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符号,它使现实和幻想之间的标志错位,使巨大的悲剧性威胁仅成为记忆。它是一种被骚扰多于骚扰的生活,是一种荒诞的社会骚动,是理性的流动”。 二、古典时代 文艺复兴使疯癫得以自由的呼喊,但驯化了其暴烈性质,而古典时代旋即用一种特殊的强制行动使疯癫归于沉寂。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哲学家们对理性的推崇和弘扬。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谈到了疯癫。他认为从他正在怀疑的这个事实足以证明,他不可能是疯子。福柯将这表述为“我思故我未疯”。思想着的主体绝不可能是疯癫的。疯癫被排除出思想——这对于像蒙田这样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来说是不可能的——标
福柯权力理论之概述
福柯权力理论之概述 在《知识分子与权力》一文中,福柯说了这样一段话,“毕竟,直到19世纪,人们才认清剥削。但人们大概永远不会知道权力是什么。可能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还不足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神秘的、被称作权力的、被到处授与人的东西。它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既是显现的,又是隐蔽的。”这段关于权力的论述多少带有一些神秘主义的色彩,这也是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所在。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权力(pouvoir)一语在福柯的著作中占据了中心地位,福柯在权力领域所作的探究,被认为堪与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领域的建树相匹,甚至福柯本人,也因而被称为“权力思想家”。但即便是这样,这段话却更像是福柯发自内心的最真实的声音,或许在他看来,其实自己和其他人一样——大概永远不会弄清楚“权力”是什么。 但是,福柯仍然尽量对权力作了最大程度上的体认,这里的“权力”我觉得更倾向于现代意义上的。他指出,权力的隐蔽性的一处重要表现就是:权力有意向却没有主体性。我个人对这句话的理解是,一方面权力的行使无不具有一系列目标和目的,另一方面这又不意味权力产生于某一个人的选择和决定。任何个人或国家机器,都不可能指挥在一个社会中产生作用的整个权力网。这也是福柯在《知识分子与权力》中所谈到的,他说,“实际上人们很不了解:谁在行使权力?在哪儿行使权力?人们几乎已了解到:谁在剥削?利益去哪儿了?然而,权力……很清楚,并不是统治者拥有权力。”这里的意思应该是指在现代社会中,并不仅仅是统治者拥有权力。因为福柯多次批评过传统的权力观念,即视权力为确保奴役一个国家国民的一组机构和机制,或者说,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实施统治的总体系统。他一再强调权力不是一样“东西”,而是一种关系,是各种势力关系的复合体,是这些势力关系通过持续不断的相互抗争,改变、增强或颠覆它们的过程。在《性史》第一卷中,福柯写道,“权力不是一种机制,不是一种机构,它不是赋予某人的一种力量;它是外借得来的一个名称,用于一个特定社会中某种策略情景。”我觉得,这段话和《知识分子与权力》中的一段话对照来看似乎更明白些,“毫无疑问,关于国家的理论和国家机器的传统分析无法穷尽权力运行和实施的领域。……凡是有权力的地方,人们都行使权力。确切地说,没有人是权力的拥有者,然而,总是一方面的一些人和另一方面的另一些人在一定的方向下共同行使权力。人们不知道谁是掌权者,但是知道谁没有权力。”权力不是一样“东西”,所以没有人是权力的拥有者。权力不是固定的存在,也不是流动的存在,而是无形的存在,是一种关系,是一
韦伯与福柯权力观之比较
·总第460期· 2012第1期理论界 □李秀玫 韦伯与福柯权力观之比较 一、韦伯与福柯权力观的出发点不同:合理化VS 解构主义 韦伯生活的时代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努力寻求发展的时期,资本主义工商业等方面需要得以充分发展的空间,探求符合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的要求的组织形式是韦伯理论的出发点。 韦伯所有研究的中心就是“西方文化特有的和独具的合理主义”这一主题,他对权力、统治的研究目的也是在于解释西方文明的突出特征。韦伯关于统治或权威类型的分析即是他关于西方合理化进程论述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1〕 福柯权力理论的形成与1968年遍及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运动有着必然的联系。革命失败的现实迫使理论家们更加深入地分析权力运作的机制,寻找一种革命之外的权力反抗模式,也让福柯陷入了对权力的深刻思考之中。 福柯的权力观体现了他后现代性的理论立场。后现代性反对关于社会的总体化的宏观观点,排斥关于社会的一致性的观念,而主张对社会的多样性、片断性、不确定性的认识方式。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认识采取了“视角主义”、“相对主义”的态度,认为理论只能提供关于对象的片断性的、局部性的、相对性的观点。〔2〕 因此,福柯是从解构 的、微观的角度来解释权力。 二、韦伯与福柯的权力概念及来源不同:政治性VS 多元性 韦伯有关权力的观点与其自身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不无关系。韦伯出生于德国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位法学家、当时政界的活跃人物,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名流会集。受父亲影响,他热衷于政治事务,而最后转向学术工作也并非他本心所愿,只是因为他的性情很难适应政治。韦伯对政治的兴趣不仅促使其作过“以政治为业”的讲演,并声明“政治就是追求分享权力或对权力的分配加以影响” ,而且还构成了他深入研究权力、统治和权威类型等政治社会学主题的重要动力。〔3〕 因此,韦伯的权力观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他对统治的关注也更多于权力。但也有学者认为,韦伯只不过是用统治的术语来讨论有关权力的问题。总之,权力和统治是韦伯政治社会学中两个十分重要的基本概念。 韦伯将权力定义为“在某种社会关系中贯彻自己的意志并排除反抗的所有机会,不管它是基于什么原因”。统治是指“在所属人员中找到服从某一具体命令的机会”。〔4〕权力和统治之间的区别在于:在第一种情况下,命令并不一定都是合乎情理的,服从也不一定就是一种责任。但在第二种情况下,人们服从为他们所下达的命令。〔5〕 福柯于1926年生于法国普瓦提埃,1984年死于艾滋病。他一生的研究都围绕着权力、知识和主体这几个概念,他的思想很多都是另辟蹊径,与传统权力观不同,他关注像毛细血管般弥漫的权力关系和细微的强制技术。 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正式提出权力分析,但在7年后福柯坦陈这篇文章中对权力问题的分析是不充分的:“到那时为止,我一直接受了传统的有关权力的概念,即把权力看成本质上是一种司法机制,它制定法律,实行禁止和拒绝,产生一系列否定的效果:排除、拒斥、否定、阻碍、掩藏等等。现在我认为这种概念是不充分的。……那是我在1971到1972年同监狱具体打交道的时候。接触了刑罚系统之后,我确信权力的问题不应该过多地从司法的角度来考虑,而应该关心它的技术、战术和战略。于是我在《规训与惩罚》中用技术和战略的分析代替了法律和否定性的概念。 ”〔6〕为更正不充分的传统权力概念,福柯将权力定义为“各种力量关系的、多形态的、流动性的场,在这个场中,产生 (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200237) 摘要:本文通过梳理比较韦伯和福柯权力观的出发点、概念及来源、核心问题等方面的不同,指出韦伯的权力观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这种权力观的关键词是权力、统治、权威类型,是一种“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权力;福柯的权力观则是渗透于日常生活的微观的、分散性的权力,他的关键词包括权力、知识、主体,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权力。最后,对权力的现实意义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韦伯;福柯;权力;统治;知识〔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47(2012)01-0028-02 [收稿日期]2011-07-15 [作者简介]李秀玫(1989-),女,安徽亳州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本科生, 研究方向:西方社会学理论。 【政治文明】 028
《毛猿》的福柯式解读
《毛猿》的福柯式解读 作者:刘慧敏 内容提要:奥尼尔的剧作《毛猿》主人公扬克的疯癫形象引起不少读者的困惑和思索,长期以来被贴上现代工业化社会异化人群的标签。实际上,扬克看似发疯的言行背后隐藏着一个社会底层人对自由的渴望和对回归人性的期盼。扬克的疯癫透过水、监狱等意象,以及疯子被展示、疯子与自恋等方面与福柯的?疯癫?视点形成映照。对扬克的疯癫解读有助于加深理解奥尼尔剧作体现出的现代悲剧意识。 关键词:扬克疯癫福柯理性 《毛猿》(1922)是尤金〃奥尼尔最令人感兴趣的剧作之一,不分幕,共8场。在关于这出戏的评论中,研究者常从象征主义的某些概念出发,探讨剧本所蕴含的人类生存价值及意义的主题,即?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的问题。奥尼尔本人在获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辞中亦强调瑞典戏剧大师斯特林堡对其戏剧创作的影响:?……对于我来说,像尼采在哲学王国一样,他将继续是我们的精神导师……?然而,通过对主角扬克的悲剧命运分析,不难发现扬克的?疯癫?与米歇尔,福柯观念里的?疯癲?竟有异曲同工之妙。借助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对?疯癫?的理解,《毛猿》可以理解为是一出探索疯癫的悲剧,这场悲剧实质上彰显了扬克完成由沉迷于?原始骄傲和过分自我?到追求真实与自由的心路历程。然而。扬克个人的努力在整个社会机制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即使是企图与兽类进行沟通的美好愿望最终也化为泡影,成为20世纪初又一幕美国悲剧。 一、奥尼尔和福柯的相通性 奥尼尔和福柯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度,但他们都从悲观哲学家尼采那里得到了几乎相同的思想观念,形成了对悲剧的相同视点。只不过一个体现在戏剧创作里,一个表述在哲学著述中。 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奥尼尔的思想较为复杂,受到希腊悲剧意识、尼采悲观哲学以及东方道教的影响。在诸种影响因素中,尼采悲观哲学无疑起着决定性作用。奥尼尔对尼采的接受,其直接原因与奥尼尔的成长经历有关。而且,尼采和奥尼尔对信仰的转变经验也有不少相似之处。 1888年奥尼尔出生在一个笃信天主教的爱尔兰家庭,7岁至13岁在天主教学校度过。奧尼尔是一个不幸的孩子,他从小目睹母亲深受毒品戕害,祈求上帝帮助却无济于事,十几岁时父母和大哥相继离开人世。目睹人间悲剧,奥尼尔伤痛不已。他开始憎恨天主教教义的欺骗与伪善,怀疑是否存在万能的上帝。最终,亲人的离去和宗教的迷失让奥尼尔丧失了归属感,陷入了巨大的困惑和悲痛之中。 1907年,奥尼尔放弃天主教已有5年,他思想困惑、对前途感到迷惘,这时尼采的哲学思想进入了他的生命。尼采的思想对奥尼尔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奧尼尔称《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对他思想的影响?超过以前他读过的任何一本书?。此后几年,奥尼尔的境遇每况愈下,他不仅真切体验到了死亡的威胁,同时对人生的理解也更加深刻。早先接触的希腊悲剧和尼釆?上帝死了?的观念在年轻的奥尼尔身上潜移默化,终于形成了奧尼尔独特的现代严肃悲剧意识。 无独有偶,从20世纪50年代直至80年代,尼采的思想对福柯的影响几乎贯其一生。在学生时代,福柯就解读过尼釆,并把尼采奉为精神导师。按照福柯的说法,1953年在他
对福柯权力理论的分析
对福柯权力理论的分析 【内容提要】权力是政治的核心,对于权力的定义域理解,古来便是见仁见智。福柯提出了权力-知识的概念,明确表示否定传统的阶级分析和阶级理论。权力不仅来自上面的结构对个人的排它性活动,而且也和知识与话语密切相关。权力和知识是共生体,权力可以产生知识:权力不仅在话语内创造知识对象,而且创造作为现实客体的知识对象。人文科学的主体,并不是由意识形态引起的幻想,而是某种权力关系现实存在的结果。新的人文科学的产生和新的权力结构的建立总是同时出现的。 【关键词】知识、权力、国家 福柯是法国哲学家、社会历史学家,后现代理论主要代表之一。其思想以反中心、反权威、反常规而著称,分析方法独特,研究主题多变,涉及历史、文学、哲学、政治、社会、文化等众多领域。福柯的权力理论强调文本与历史的关系,把权力当成具有心理意志力的普遍欲望。认为权力是档案负面的社会、政治现实,是一种永远存在、无法摆脱的社会罪恶。知识和权力是密不可分的“共生体”。知识是表象,权力是实质。每一种话语实践都有一套规则,以潜在的权力形式支配着特定领域的知识、思考和写作。历史写作的话语是在权力斗争中产生的,权力是人们对于事物所实施的暴力。不存在纯粹客观的话语,只有体现或大或小权力的话语。在艺术领域,一如政治、历史中,通过掌握话语而获得权力。福柯认为,权力不是获得的,也不是分享的,而是通过各种关系的一种转换无定的游戏,这些关系涉及经济、政治、知识、情感、性等各个领域。权力有意向却没有主体性,即便是权力促生了反抗力量,但它也只能存在于权力关系错综复杂的游戏网之中。 自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人们就对权力进行着持续而深入的研究。可以说,权力是一个既古老而又崭新的话题,从古希腊的先哲们到现当代的思想家们都在孜孜求索。然而,权力却是一个在本质上具有争议的概念,又具有多张面孔,学者们见仁见智,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理解。权力问题既是一个政治学的问题,又是一个法学的基本问题,虽然权力问题由来已久,但是关于权力的问题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而且在这些权力问题的论述中最为关注的是统治权问题,即统治权的合法性问题,谁掌握统治权的问题,统治权问题一直是西方权力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权力是政治的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研究就是关于权力分配方式和运行机制的研究,政治学也就是关于权力的学问。 福柯对于权力的定义独树一帜,福柯认为权力是档案社会的政治侧面,是一种无所不在、无法摆脱的社会事物。1972年他在知识分子与权力一文中说:那东西如此神秘,可见有不可见,在场又不在场,无所不在无孔不入,这东西就叫做权力。对福柯而言,权力不只是物质上的或军事上的威力,权力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权力和知识的关系。“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的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即能够表现出来有知识是权力的一种来源,并引进了“话语”的概念。这里的“知识”有更广泛的含义,即人们对整个世界认知。福柯认为人们只有精通某一领域的知识才具备了这个领域的话语权,同时,这一领域的知识只有被普遍承认,才能转变成“权力。 福柯悬置了权力的本体论以及权力的合法与非法这一问题,可以得出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法治的着点被悬置了。在传统自由主义看来法律是用来确定权力获得的合法性问题,以及限制权力的滥用的,这些法律的合法性同样也来自更深刻的合法性,在福柯这里传统自由主义的主张变地没有说服力了,甚至是变地不现实了。福柯批判了理性的霸权地位,同样否认法律的全能性与完备性,那种在权力面前无可置疑的法律在福柯看来是不存在的。与启蒙时期的法学家不同,福柯不认同那种对法律进行的客观分析,试图探讨法律的真实处境,运用历史-政治话语来分析法律的起源问题,法律之所以为法律的标准问题,以及法律的中立性问题。
论福柯的权力观1
论福柯的权力观 ——读《规训与惩罚》 摘要 本文通过对福柯微观权力的分析,指出福柯是用一个我们所不注意的方式将现代性的反面突出出来,从而达到他所要实现的对于现代性的批判的目的。福柯将权力作为主导要素视为问题的切入点,运用“系谱学”方法将隐藏在“自由”社会本身的微观权力揭示出了,指出的微观权力的隐匿性与生产性的特征。微观权力就隐藏在社会运作体制之中,隐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并且生产出了我们所认可的真理与知识,并且形成了规训社会。面对这样的规训社会,我们是否有“自由”可言,作为主体的本真性如何表达出来。因此随后分析了微观权力与反抗的关系,在对福柯的个体的反抗的进一步分析中指出,他的反抗模式在理论上可能存在反抗标准模糊的可能性以及个体之间、个体与整体之间冲突的可能性,从而在理论上存在危险。同时在实践中,也对福柯提倡的大众生活的日常反抗的实践效果的可行性与个人的审美体验进行了质疑。本文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表达了福柯对现代性的批判;第二部分,着重对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的权力观进行梳理,着重找出福柯认为从酷刑到微观权力产生的历史的原因和为我们揭示出了我们所不注意的、深处其中的微观权力的“系普学”研究方法。然后,着重分析使微观权力得以弥散整个社会的“规训”的技术手段,以及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具有的特点和它与传统权力观的区别;第三部分,权力与自由、权力与反抗的关系,着重从他的微观权力理论与反抗的关系人手,分析福柯的反抗理论的可行性是否存在。 导言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l926—1984)[1]是20世纪西方知识界最引人注目的核心人物之一,福柯与让-保尔·萨特、莫里斯·梅洛-庞蒂、乔治·冈奎汉姆、路易·阿尔都塞、雅克·德里达、克德·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吉尔·德勒兹等人一起,揭开了法国哲学、美学与政治思潮中革命性的篇章,从60年代到80年代,短短30年时间中产生了辉煌的著作,这些成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福柯作为一个后现代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则其地位更是突出。 福柯不是一位思想始终如一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始终在变,他的研究对象以及使用的方法也在变化[2]。而在这些研究的变化中,不变的只是他从尼采那里继承下来的对于“人的问题”的思考,即“我们是谁”,并且对于“自我”[3]的追寻是与对现代性的批判反思相伴随的。福柯认为,在理性复苏之后,人们不是随着主体意识的建立变得更加自明了,而是更加陷入到了现代性的束缚之中,主体不能摆脱现代化发展中给我们加入的制度性的限制,而变得更加没有自我了。 那么,主体如何认识到这种“不自我”的状态呢?如何研究主体问题呢?福柯选择的研究路径是通过权力来研究主体。为什么要从权力入手呢?这里就暗含着福柯对于“权力”不同于传统人们对于权力的认识,即他认为现代社会中存在着微观权力,它隐藏在我们生活与工作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中,它伴随着规训“机制”浮在我们的面前,并且这些“机制”逐渐地变成我们“理所当然”的东西,所以我们很难察觉到它的存在。而福柯就是要将它揭示出来,从而可以达到它对于自我的真正认识,这是福柯一生要达到的目标,也即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所说的:“如果这意味着从现在的角度来写一部关于过去的历史,那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如果这意味着写一部关于现在的历史,那才是我的兴趣所在。”① ①【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三联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
有关福柯话语理论的文献综述.
有关福柯话语理论的文献综述 以“福柯话语理论”为关键词在万方数据库搜相关文献共119篇,分类得与理论相关的文章33篇,用于文学作品与文学人物分析共34篇,与文化相关的共10篇,理论联系现实的共13篇,与翻译中的话语权力有关的文献共11篇,此外与教育有关的有6篇,其他话语理论的学者的文献4,其他学科有8篇,下文将对文献分类整理。 一、福柯话语理论 (一)相关文献资料 编 号 标题作者出处日期摘要 1.“人之死”何 以成为可能 ——试论福 柯的话语主 体理论黄华北京 行政 学院 学报 200 9年 第5 期 福柯的“人之死”提出的背景、话 语/主体——解构主体的方法论、 “人之死”的含义、话语住体理论 的评价 2.“政治解剖 学”——福柯 权力观论略陈缘上海 师范 大学 硕士 学位 论文 200 9年 4月 建构福柯权力哲学的逻辑,即:经 验~知识一权力;身体一主体一权 力;理性一非理性一权力。认识理 性与权力的关系,使规训不再成为 一种压制或奴役的新方式,而是作 为变革现代性缺陷的途径等。
3.从“人之死” 到“作者之 死”——福柯 作者理论探 析董树 宝 江西 社会 科学 200 9年 3月 人是现代知识型形构的产物,作者 也是现代知识型形构的产物。当代 书写还改变了传统书写与死亡的关 系。 4.从福柯对主 体性的批判 看其文学观张娜华东 师范 大学 硕士 学位 论文 200 6年 4月 以福柯批判主体性为出发点,审视 了福柯理论中最重要、最基本的问 题:主体、话语和权力,并透过福 柯对这些基本问题的哲学论述的思 维方式来探究福柯理论中散现的文 学观点。 5.从批评性话 语分析看福 柯的话语理 论吴继 宁 考试 周刊 200 9年 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视角对福柯建 筑于知识考古学和系谱学基础之上 的话语及其话语分析理论框架进行 了简要的分析说明。 6.福柯“话语” 概念之解码陶微 希 安徽 大学 学报 200 9年 3月 话语定位于以“异位”为开端的知 识型的空阀构型之中;话语由实践 性的陈述整体构成;来源、间断性 和离散性成为话语的主要原则。在 此概念中,福柯反传统历史现、反 西方现代文明的思想得到了充分展 现。
[马斯,福柯,现代性]福柯与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的争论
福柯与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的争论 福柯和哈贝马斯之间的争论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界前沿的一次伟大争论。在西方,对待现代性问题上,福柯和哈贝马斯代表了两种绝然不同的立场。福柯是现代性最著名的批判者,而哈贝马斯却是现代性最著名的辩护者。对于这次论争,前人也做过大量的研究,他们从不同的侧而对福柯和哈贝马斯之间的论争进行了分析。总体上说来,主要是从福柯和哈贝马斯的理论来进行的比较研究,最终见出二者在理论上的差异。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仅仅是对福柯和哈贝马斯之间的理论比较,而没有发现二者论争的实质,更没有解决二者为什么会争论的原因。 福柯和哈贝马斯是在现代性这个问题上进行争论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尽管今人无法给现代性一个确定的界限和定义。对于现代性,安东尼吉登斯说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现代性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在它的内部包含着丰富的而又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从不同的方而分析就会有不同的结论。要真正分析清楚福柯和哈贝马斯之间的论争,还必须回到现代性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一、现代性的根源 现代性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是相对于前现代而言的。在前现代时期,时间和空间是统一的,二者在所指上具有一致性。前现代时期,没有统一的计时工具和可见的机械钟,对大部分的人而言,时间和地点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参照地点空间才会分清楚与自身相关的时间。事情总是和某个地点相联系对大部分人而言,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都是受在场的支配,即地域性活动支配的。随着现代机械钟的出现,时间逐渐变得精确,人们在辨别事物的时候不再是以地点作为基点,空间逐渐变成一个不确定的对象。空间变成一个不确定对象,时间也逐渐变得虚化。每个人都确信有着自己的空间,但无法从流动、变化、转瞬即逝中的事物中找到依靠。现代性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让每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现代同传统的决裂,传统的稳固性在时间里支离破碎,时间由零碎逐渐变成统一,空间迅速地膨胀,这是现代性出现的重要标志。 时钟让无法掌握的、流动的时间变得有掌握的可能,让盲目的人变得自觉起来,确定具体的上下班时间。这种统一时间的情况最初只是出现在某一处,渐渐地扩展,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虚化的时间让掌控空间变得可能。 统一时间是控制空间的基础。时间已经虚化,由完全无拘无束的自由状态变成了可以掌控的形式在前现代社会,空间和地点总是一致的。时钟让人可以感觉到时间在流动,让一切变得转瞬即逝,传统不断被颠覆,不断地膨胀着空间。 时间和空间的分离,时间变得可以掌控,空间无限地膨胀现代和传统之间的界限变得愈加模撇现代的机器大生产、大工业通过技术、空间生产,使现代从传统中断裂,现代性的时间得以呈现;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使传统的、固定的、稳定的空间进一步打破,全球化的影响得以出现。现代性正是来源于此。 二、现代性的呈现
韦伯与福柯现代性理论的比较 - 中国社会学网
韦伯与福柯现代性理论的比较 刘梦阳① (云南师范大学 哲学与政法学院,云南 昆明650091) 摘要摘要::韦伯与福柯都是讨论现代性的大家,韦伯将现代性的负面比作“理性的铁笼”,而福柯将现代性对人们的监控看做是“全景监狱”。但是将二者的现代性理论放在一起比较的研究却很少。他们各自的理论有其显著的特点。二者在在现代性思想方面的差别主要集中在方法论、分析视角、对待现代性的态度和关注焦点这四个方面的不同。但是殊途同归,二者都对现代性进行有逻辑、有价值、有深度的批判。但是二者都剑指现代性的症结却都没有提出超越的方案和设想。 关键词关键词::马克斯·韦伯 米歇尔·福柯 现代性理论 一、引文 提到现代性理论,学者们一般会把福柯与马克思、福柯与哈贝马斯、卡尔·马克思与马克斯·韦伯进行比较,但将韦伯与福柯二者放在一起比较的却几乎没有。他们一个是经典社会理论家,一个是后现代理论家(虽然福柯本人不认同这个说法);一个中规中矩,一个剑走偏锋。乍看上去二者的理论、思想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是韦伯和福柯都是讨论现代性的大家,比较二者的现代性思想确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二者理论既截然不同,又殊途同归。使二者的现代性理论碰撞,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火花。下面进行详细的分析。 二、福柯与韦伯现代性思想的差异 (一)方法论的差异方法论的差异::理想类型与系谱学 韦伯的学术研究都是在他的理想类型的方法论的指导下展开的。韦伯的理想类型意味着“每一种定义都不是要穷尽性地描述推理和社会的特殊情形,而是要提供一个概念框架。”[1] P33理想类型是研究的“工具”,而非社会“模型”。 ① 作者简介:刘梦阳,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社会学专业研究生。
福柯与马克思: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福柯与马克思: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ichel Foucault and Karl Marx is complicated :their dialogic relevance sometimes embodies the opposite. Marx attaches importance to material practice to explicate the formation of idea on the explanation of historical phenomena ,while Foucault emphasizes on explanation plurality and contradiction ,and the role of paradigm in explaining. Both Foucault and Marx are concerned with the issue of governance on modern types of capitalism. Foucault's understanding of power is relevant to Marx's ,but he focuses on exploring microphysics of power and power's operation strategy ,instead of economic power ,material power and national power on a grand scale. 福柯的学术发端于20 世纪60 年代这一反叛的年代,受到尼采 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尼采对理性、知识、主体、进步观念的质疑,以及 认为求真意志与权力意志不可分的思想的影响,这是学界所公认的, 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福柯成长和学术思想发生发展的时期,也是马 克思主义在法国影响巨大的时期。他在读大学时,“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阿尔都塞便是他的哲学辅导老师。福柯与马克思的关系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西方有
知识分子与权力 ——福柯与德勒兹的对话
《福柯文选》第8部分 原文:'Les Intellectuels et le pouvoir' (Intellectuals and Power) 译者:吕文江 校者:应星、张广生 字数:8723 说明:本文是福柯与德勒兹的一次对话,最初于1972年3月发表于L'Arc, no.49,后又于同年5月发表于Le Nouvel Observateur,英译本收入了《语言、反记忆和实践》一书中。中文翻译主要依据英译本,并参考了法文本。 知识分子与权力 ——福柯与德勒兹的对话 福柯: 有位毛主义者曾对我说:“我很容易理解萨特站在我们一边的意图。他之所以卷入政治,他的目的何在,这都不难理解。我也能部分地理解您的立场,因为您一直关注的是禁闭(confinement)问题。但德勒兹却是一个谜。”这番评论使我颇感吃惊,因为在我看来,您的立场似乎一直是相当明晰的。 德勒兹: 我们今天或许正在目睹理论与实践之间一种崭新的关系。实践有时被认为是对理论的应用,是理论的后果;有时则具有相反的意义:人们认为它可以激发理论,是创造新的理论形态所不可或缺的。但不管怎样,人们都是从总体化(totalization)的过程来理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但我们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即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要局部与零碎得多。一方面,理论总是局部性的(local),它与某个有限的领域联系在一起,它虽然也可以被应用在其它的领域,但这些领域与它或多或少有着距离。理论的应用绝非照猫画虎的(resemblance)关系。不仅如此,从理论进入它适用的领域那一刻起,它就会遭遇到种种的障碍、屏障和堵塞,这一切都要求理论被另外一种类型的话语所替换,(正是经由这种替换后的话语,理论才最终进入了不同的领域)。实践就是一个从一种理论观点到另一种理论观点的“驿站”(relay)系统,而理论则是一种实践与另一种实践之间的一个“驿站”。任何一种理论如果碰不到屏障,就不可能有所发展;而要穿透这一屏障,实践就是必不可少的。譬如,您的研究始于对监禁的社会背景的理论分析,其中着重关注的是某一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病院。在那里,您开始意识到那些被监禁的个体为自己讲话,创建一个“驿站”的必要性(也有可能正相反,您所发挥的作用对他们已经起到了“驿站”的作用)。你在监狱中发现了这种群体——那些在监狱里被囚禁起来的个体。为此,您组织了监狱调查小组(G.I.P.: group of informatam on prisons),1旨在创造让犯人自己能讲话的条件。如果象上面那位毛主义者所暗示的,您通过投身于实践而践行了自己的理论,那就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说法。这并非是对理论的应用,也非传统意义上的倡导改革或调查项目。这里所强调的是全然不同的东西:在一个广阔得多的领域里面的“驿站体系”,这个领域由各种复杂多样、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部件构成。在我们看来,进行理论研究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成其为某一主体,不再成其为某种代表什么或有代表性的意识。尽管某个小集团或工会仍将代表那些行动者和抗争者的意识的权利据为已有,但他们实际上已不再能代表那些人了。究竟是谁在 1“Group lnformation des prisons”:福柯著作《我,皮埃尔·里维埃……》及《规训与惩罚》源自于这一组织。
哈贝马斯与后现代
哈贝马斯与后现代 管理学院08级人力资源管理 刘辉丽200800250029 摘要:本文主要介绍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认识及其主要思想,演绎了哈贝马斯的思想世界,并介绍了他对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进行的强烈批判。 关键词:哈贝马斯现在性后现代法兰克福学派福柯 哈贝马斯简介 但凡听过法兰克福学派的人,必定听说过一个名字——哈贝马斯,作为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可以说是批判学派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旗手。哈贝马斯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研究方面可谓成绩卓然,而他本身亦是一个不凡的人。1961年完成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后历任海德堡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以及德国马普协会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长。 哈贝马斯批判思想 关于哈贝马斯的批判思想的发展,可以总体规划为两种。19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他的批判视角主要在于“工具理性”,强调其“公共领域”理想模型。进入70年代后,他的批判视角逐渐从“工具理性”转向了“交往理性”,这一时期他的主要著作有《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交往与社会进化》、《交往行为理论》、《道德意识与交往行为》等。而哈贝马斯这种在“理性”批判视角上的转变,亦离不开其所构建的“公共领域”理想模型,二者密不可分。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哈贝马斯不但以系统严谨的社会批判理论对主体理性进行了剖析,同时也对后现代主义者的反理性进行了深刻反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公共领域”、“交往行为”等创新性理论,试图以
此重建现代性理性秩序,而这些思想、理论都是西方学者研究现代性、后现代性的重要资源。 在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哈贝马斯不仅以严整的社会批判理论为基础对主体理性进行了剖析,而且也对后现代主义者的反理性进行了反驳,并且在此基础上试图重新构建现代性的理性秩序,以实现他对现代性的支持。面对现代文明的发展,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思想家所坚持的“现代社会里,终极价值的隐退终将造成意义的飘散、人性的压抑和自由的沦陷,这是现代人所无法逃避、无法克服的现实”的悲观失望的态度,哈贝马斯则对此持以乐观向上的态度。不同于黑格尔、尼采对于现代性批判的途径,哈贝马斯强调现代性理性视野应该突破传统的理性的反思批判,从而加大现代性重建的可能性。而哈贝马斯认为理性重建的主要方法就是“公共领域”的构建,也就是建立一个民主的、平等参与的、自由讨论的整合社会,从而使人们在平等的交往基础上达成相互理解与意见一致,缔造没有暴力没有压制,自由而和谐的共同生活,进而建设现代化民主国家。 除上述关于现代性的理论研究之外,哈贝马斯的知识旨趣说、技术统治论和沟通行动论等学说,作为综合的社会批判理论,都对西方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知识旨趣学说上,他认为知识的产生源自于人类的三种旨趣,而对历史一解释知识、经验一分析知识和技术控制旨趣的统治地位的否认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主要凶手。而在沟通行动论学说上,他则认为,真正、完善的批判理论必须重视互动过程和沟通过程,只有通过沟通行动才有可能把人类从被统治中解放出来,才能真正克服现代社会的动机危机和信任危机。 在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各种摩擦冲突不断,作为法兰克福学派两代人的代表,哈贝马斯与霍克海默之间围绕着对“经验与规范”以及“革命”的理解所展开的冲突显得格外引人注意。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些摩擦的存在,才促使哈贝马斯在思想理论的发展上有更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和思考,最终为整个西方现代思想做出了杰出贡献。 后现代 在现今社会,“后现代主义”一词可谓是家喻户晓了。各类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文章、电视节目等汗牛充栋,在那些知名的国际大都市,从发型设计师到时装营销员、从建筑师到出租车司机,各行各业几乎每一个人都听过后现代主义,
福柯与萨义德_从知识_权力到异文化表述
福柯与萨义德:从知识-权力到异文化表述 张兴成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异文化表述或再现问题的讨论来看萨义德与福柯思想之间的联系与断裂。主要分析萨义德在运用福柯的知识—权力话语的“理论旅行”过程中获得的洞见及堕入的方法论陷阱。尤其是从文学的角度来探讨话语分析方式给萨义德的东方主义问题带来的矛盾和困境,从而对东方主义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萨义德在论证逻辑上的不足作进一步批评。 关键词 东方主义 知识—权力 表述(rep resentation) 《东方学》自1978年问世以来,已经在许多国 家、语种、学科中产生了广泛持久的影响。萨义德(Edw ard.W.Said)在书中阐释的“东方主义”(O rientalis m)话语触及到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冲突中的诸多问题,“东方主义”成为讨论殖民时代以后全球状态的“关键词”(key wo rds)。萨义德通过对东方主义话语的分析与批判,“力图提出与探讨人类经验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人们是如何表述其他文化的?什么是另一种文化?文化(或种族、宗教、文明)差异这一概念是否行之有效,或者,它是否总是与沾沾自喜(当谈到自己的文化时)或敌视和侵犯(当谈到其他‘文化’时)难解难分?文化、宗教和种族差异是否比社会经济差异和政治历史差异更重要?观念是如何获得权威、‘规范’甚至‘自然’真理的地位的?知识分子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他是否只是在为他所属的文化和国家提供合法证明?他必须给予独立的批评意识,一种唱反调的批评意识有多大重要性?”①这些问题至今仍纠缠着知识界。本文企图从异文化表述问题出发,对东方主义话语的理论前提与方法问题作批判性探讨,以凸现东方主义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萨义德“理论旅行”的意义。 一 萨义德在《理论旅行》(T raveling theo ry)一文中探讨了理论在不同时空中 的移动问题。他关注一个观念或一种理论从此时此地向彼时彼地运动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自身的力量,一定历史时期和民族文化的理论放在另一时期或环境里,是否会变得面目全非。他强调必须重视理论使用的历史情境,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思想事件所由发生的特定社会历史情境的回应。批评家必须在借鉴理论的同时反思理论,拒绝“不加批评地、重复地、毫无限制地”使用任何一种理论,否则,“看似方法论的突破可能很快就变成方法论的陷阱(雷蒙德?威廉斯)”②。在此,我们要追问的是,萨义德本人在理论的使用中,是获得了“方法论上的突破”,还是堕入了“方法论的陷阱”呢? 萨义德的认识论基本是历史主义的,他承袭了从维科到黑格尔、马克思、狄尔泰、斯宾格勒以来将历史看做是人的创造的观点。在方法论上他采用了 天津社会科学 2001年第6期① ②萨义德:《理论旅行》,见《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韩刚 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151页。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