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探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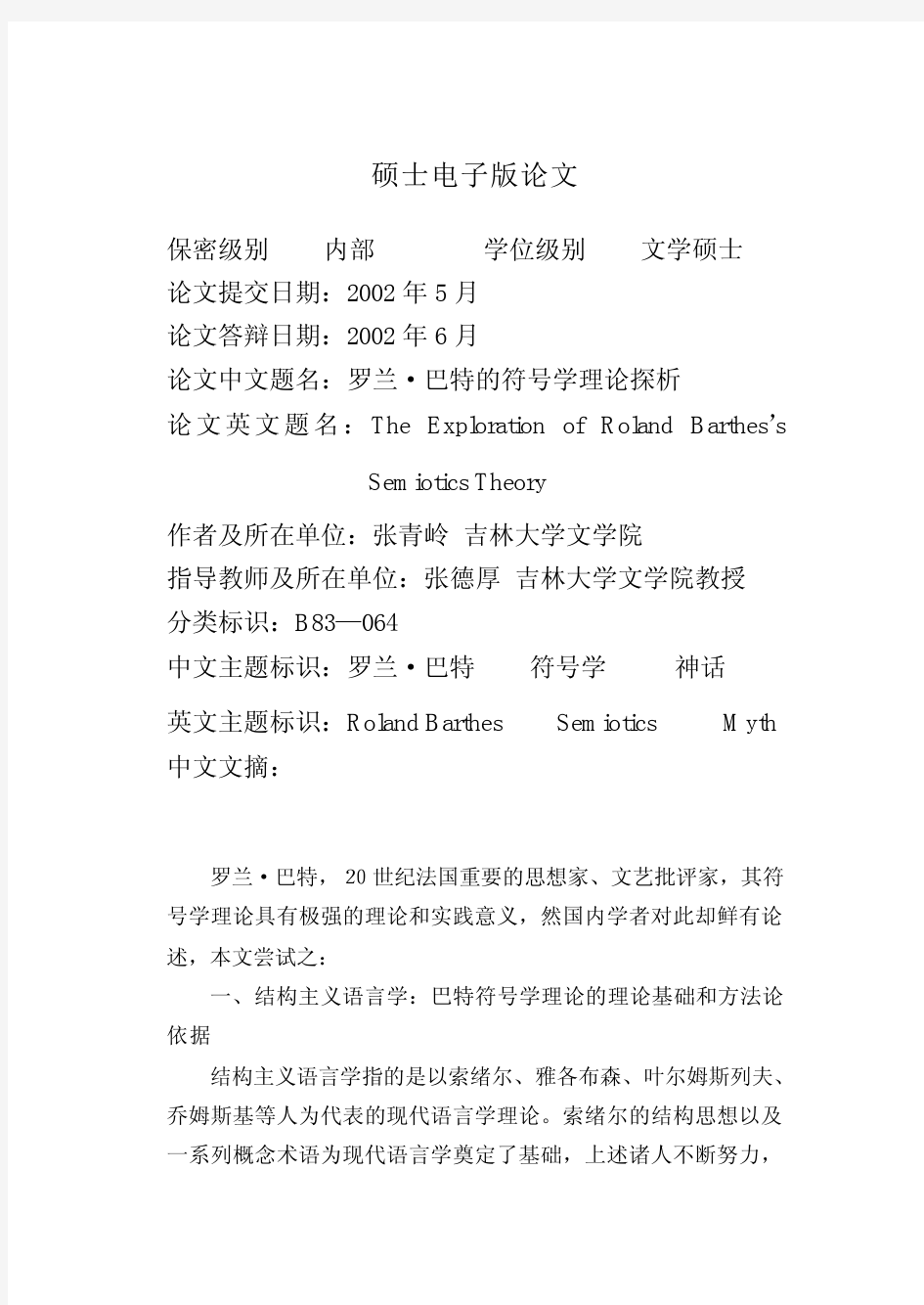

硕士电子版论文
保密级别内部学位级别文学硕士
论文提交日期:2002年5月
论文答辩日期:2002年6月
论文中文题名: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探析
论文英文题名:The Exploration of Roland Barthes’s
Semiotics Theory
作者及所在单位:张青岭吉林大学文学院
指导教师及所在单位:张德厚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
分类标识:B83—064
中文主题标识:罗兰?巴特 符号学 神话
英文主题标识:Roland Barthes Semiotics Myth 中文文摘:
论文摘要
罗兰?巴特,20世纪法国重要的思想家、文艺批评家,其符号学理论具有极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然国内学者对此却鲜有论述,本文尝试之:
一、结构主义语言学:巴特符号学理论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依据
结构主义语言学指的是以索绪尔、雅各布森、叶尔姆斯列夫、乔姆斯基等人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理论。索绪尔的结构思想以及一系列概念术语为现代语言学奠定了基础,上述诸人不断努力,
完成了语言学上的革命。
巴特符号学理论中处处可见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一系列概念、术语、完全来自语言学,理论体系也是依照语言学的理论体系而建立,而且巴特用来分析社会中诸现象的符号学方法也来自语言学。
由是观之,巴特的符号学理论完全建基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之上,继承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优缺点:形式性、科学性、可操作性和非历史性。
二、语言乌托邦:巴特符号学理论的理论实质
巴特的符号学理论在20世纪西方哲学、美学的语言论转向中具有严格意义上的语言乌托邦性质。语言乌托邦,本文中,有三层含义:(1)语言性,语言模式是巴特符号学理论的第一性原理,他甚至颠覆索绪尔的假设,以符号学为语言学的分支;(2)乌托邦性,即幻想性,从零度写作到符号学大厦、元语言,均具有浓郁的理想化色彩;(3)语言乌托邦性,“意为语言性或语言论乌托邦,亦即符号性或符号论乌托邦。我们用它指20世纪西方美学的语言理想范型崇拜倾向,这意味着关于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或现代传播媒介问题的探索,被认为是解决美学问题、探索审美和艺术奥妙的理想途径。” 巴特认为语言和文学是同质的,二者互为乌托邦。
然而,巴特符号学理论的建构中也包含着解构的力量,庞大的符号学大厦中隐藏着裂缝,因为语言不仅是乌托邦,也是法西斯。当巴特对语言的崇拜达到极端时,必然走向它的反面,反语言,反乌托邦。
三、神话和解神话:巴特符号学理论的社会学主题
“神话”一语,出自巴特的《神话》,巴特从语言学的角度对
其做了界定:首先,神话是一种言谈,一种讯息,它不是由讯息的客体而是由说出讯息的方式来定义的;其次,从意义构成的角度看,神话是一个二级符号系统,“其中一个系统成为另一个系统的能指”。巴特还指出,神话是一个“去政治化的言谈”,因此,“解神话”在巴特那里首先是,指出资产阶级如何以匿名的方式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所有社会阶层之上;推而广之,“解神话”就是指出神话的运作方式以破除迷思。
“解神话”的理论武器是含蓄意指符号学。含蓄意指和元语言均是二级符号系统,不同的是,含蓄意指是一个系统成为另一个系统的能指,元语言是一个系统成为另一个系统的所指。前者用来分析意义的构成,后者为现象命名。
巴特首次成功地将符号学用于当代大众文化分析,显示了符号学理论的现实批判意义,对后来的大众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巴特符号学理论对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意义和局限
巴特将符号学用于大众文化研究,独开大众文化研究的符号学一派。在西方,巴特的符号学研究方法已融入众多学派之中。对中国而言,其意义可作如是看:方法借鉴意义和思想解放意义。其局限表现在:符号学解释在经验上的有效性难以证明;精英主义立场,看不到大众在神话接受中的反抗力量;形式化倾向,只注重意义分析,缺乏社会理论基础的支持。
总之,巴特对符号学的贡献有二:一是初步建立了一门符号科学;二是将符号学用于大众文化分析,显示了符号学强大的社会批判和阐释力量,后者的意义尤其巨大。巴特的解神话思想会同福柯、德里达等人,引发了一场后结构主义风暴,在人类思想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
英文文摘
ABSTRACT
Roland Barthes is a well-known thinker and literary critic of France in 20th century, and his semiotics theory has profound theoretic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But in China few of people spend their time on the study of Roland Barthes’s semiotics theory, th e author intends to try on it:
Part one:Structuralism linguistics: the basis of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Barthes’s semiotics theory
Structuralism linguistics refers to modern linguistics theory represented by the following linguists such as Saussure, J akobson, Hjelmslev, Chomsky, Benveniste etc. Saussure’s structural thought and a series of concepts based a basis for modern linguistics. Under his influence, the above-mentioned figures accomplished a revolution in linguistics, and the revolution affected other disciplines.
Barthes’s semiotics theory is filled with linguistics traces. Firstly, a series of terminology in it are come from Structuralism linguistics; Secondly, the system of barthes’s semiotics is completely based on Structuralism linguistics; Lastly, the method barthes using to analyses social signs results from linguistics.
Because Barthes’s semiotics imperial is completely based on structuralist linguistics, it ha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Structuralism linguistics, for example, formality, scientificity, practicality and contrary to history.
Part two: linguistic utopia: the essence of Barthes’s semiotics theory.
Barthes’s semiotics theory appears clearly linguistic utopia nature in the linguistic turn of 20th in west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Linguistic utopia has three meanings: I Language nature. Linguistic model is the first principle of barthes’s semiotics theory, further more, he overturned Saussure’s view and advocated semiotics is a branch of linguistics. II Utopia nature. From ‘zero writing’ to sign imperial and meta-language, all of his semiotics thoughts are charged with idealism. III Linguistic utopia nature. As Mr.wang Yichuan said, ‘it means language or linguistic utopia nature, or sign utopia, we use it to signify the worship tendency to linguistic model in west aesthetics of 20th century, which implies that the exploration about linguistic, nonlinguisticsign or modern media is considered as an ideal way to resolve the problems of aesthetics and art.’ Barthes considered literature is the utopia of language, and language is the utopia of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s identical in essence.
Language is not only utopia but also fascist, the breed of deconstruction is contain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inguistic utopia. When Barthes’s worship to linguistics had been on its peak, he must go to its reversal side: anti-language, anti-utopia, and this is the late Barthes.
Part three: Myth and Demythfication: the sociology theme of Barthes’s semiotics theory.
The term Myth is originated from Mythologies. From the angle of linguistics, Barthes identified as follows: firstly, Myth is a parole, a message, and it is not identified by the message itself but the way it is said; secondly, Myth is a sign system which is made of two arrangements, one of them is the signifier of the other. Further more, Barthes regarded Myth as ‘parole depolitization’, so the term
Demythfication primarily means in Barthes’s books revealing the fact that how the bourgeoisie imposes its ideology on all other classes by the means of concealment. Likewise, Demythfication means pointing to the procession of mythicization in order to do away with blind faith.
The arm of Demythfication is connotation semiotics. Connotation and Meta-language is a sign system that is made of two arrangements. Connotation signifies one of two sign system is a signifier of the other; “meta-language” signifies one of two sign system is a signified of the other.
Barthes applied semiotics to analyses popular culture forms, this showed that semiotics has practical and critical significance, and it has made profound influence on popular culture study at the present day.
Part four: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Barthes’s semiotics theory to contemporary popular culture study
Barthes connected semiotics with popular culture study, and initiated semiotics school of popular culture study. His semiotics method has merged into other schools of popular culture study in the west. For China, the significance of Barthes’s semiotics is that we can use his semiotics method for reference and promote the liberation of idea. But the limit of Barthes semiotics is quite clear: firstly, its validity in explanation of social signs is not be proved; secondly, Barthes stood for elitism, he couldn’t notice mass’ strengthens; lastly, it has formalization tendency, and short of the basis of social theory.
In short, Barthes’ s contribution to modern semiotics may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initiated the semiotics discipline and applied semiotics to analyses social signs. His demythfication thought together with Foucault, Derrida, has launched a revolution to west metaphysics tradition, and will exist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thought.
总页数:28页
开本有图表
前言
在英语中,符号学有两种称谓:semiology 和 semiotics。前者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管它叫符号学。它将告诉我们符号是由什么构成的,受什么规律支配。……语言学不过是这门一般科学的一部分,将来符号学发现的规律也可以应用于语言学,所以后者将属于全部人文事实中的一个非常确定的领域。”[1] 后者为美国学者皮尔士(Peirce)创立,“我认为我已表明,逻辑学在一般意义上只是符号学的别名,是符号的带有必然性的或形式的学说”。[2](在符号学的发展中,二人的思想已交汇。)国内将二者均译作符号学。[3]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前,符号学只是一种设想,后来,人类学家、文学批评家和其他研究者受到语言学家的影响,设法从其观点中受益,于是发展了索绪尔早先假定的符号学科学。[4] 关于符号学的定义,目前学界尚无定论,一般认为,符号学是从现代语言学模式引申而出的,关于人类符号活动的一般规律的总的学科(或研究领域),它主要研究意义的产生、传达和诠释过程。六十年代以后,符号学又有了新的发展,几乎覆盖了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是结构主义符号学最早的拥护者,1977年,他也是以“文学符号学”家的身份登上法兰西学院的讲台的,虽然巴特在就职演讲中强调说,他个人的符号学与他曾促进过的那门符号学科相比,是颇带随意性的,如果说不是正相对立的话。[5]
巴特在《罗兰?巴尔特谈罗兰?巴尔特》中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神话社会”阶段,代表作是《写作的零度》、《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以下简称《神话》)和关于戏剧的文章。其思想可与萨特、马克思、布莱希特等人互相参照。
第二阶段为“符号学”阶段,代表作是《符号学原理》、《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以下简称《流行体系》)。其思想可与索绪尔互相参照。
第三阶段为“文本性”阶段,代表作是《S/Z》、《萨德、傅立叶、罗耀拉》、《符号帝国》。此时他的思想与索莱尔(Sollers)、克里斯蒂娃(Kristeva)、德里达(Derrida)、拉康(Lacan)等人相互参照;
第四阶段为“道德”阶段,代表作是《文本的愉悦》、《罗兰?巴尔特谈罗兰?巴尔特》。他的思想可追溯到尼采。[6]
巴特自己仅将第二阶段列为符号学阶段。笔者认为,巴特的符号学思想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在《写作的零度》中巴特已显露出符号学思想的痕迹。他在导言里说:“埃贝尔在开始编写每一期《杜歇纳神父》的时候总要用一些‘见鬼!’和‘妈的!’字眼。这类粗俗字眼并不意指着什么,但却表示着什么。为什么呢?这是当时整个革命情势的需要。”[7] “意指”和“表示”指出了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的不同,预示了《神话》中的“外延”(直接意指)与“内涵”(含蓄意指)这对概念。从《神话》开始及整个六十年代,一方面,他倾注心血于符号学理论的建构及以其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批评;另一方面,他用符号学中的结构观念分析文学,提出了“文学科学”的概念,并对叙事文学作品的结构做了详尽的分析。
《流行体系》之后,巴特宣布他告别了符号学,认为这是他“科学化的美梦”,然而,我们看到,符号学已成为他思想的一部分。符号学的概念,如符号、能指、所指、代码以及符号学的结构分析法、对意义的关注在他以后的作品中不断出现。《S/Z》将巴尔扎克的中篇小说《萨拉辛》分解为561个单位,归为五种代码,可看作文本符号学。《符号帝国》中对“空的记号”大加赞扬。一直到后期,巴特谈论快感、谈论享乐、谈论制作一种无权势的话语时,仍显示了他对符号及意义的浓厚兴趣。
由是观之,符号学思想贯穿了巴特的一生。他“构造‘我们时代的可理解性’,即去发展处理过去和现在诸现象的理智构架”。[8]就狭义而言,罗兰?巴特的符号学思想指的是从《神话》开始的六十年代他对符号学理论的建构以及以其作为方法和基础对社会文化现象的分析,这正是本文探讨的重点,笔者将其称作符号学理论。
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具体体现在《神话》(1957)、《符号学原理》(1964)、《流行体系》(1967)这三本著作中。其理论以对符号学的借用始,以对符号学的应用终,中间经过一个理论建构期,显示出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国内对巴特的研究以文论为主,鲜有专论其符号学思想的。[9]而在国外,由于巴特将符号学应用于当代通俗文化研究,“陈述了一种解释通俗文化的方法,从那时以来,它几经显著改动,被广为研讨,影响极大”。[10]笔者有感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繁荣,拟就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做一全面解析,指出它在大众文化研究方面的意义与局限,就教于方家。
一、结构主义语言学:
巴特符号学理论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依据
巴特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启发,将语言学的诸概念移入符号学领地,搭起了语言学到符号学的桥梁,初步建立了一个用于分析社会生活中诸记号的符号学体系,将索绪尔的设想变成现实。
结构主义语言学,指的是以索绪尔、雅各布森、叶尔姆斯列夫(Hjelmslev)、布龙菲尔德、乔姆斯基(Chomsky)、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等语言学家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理论。在上述诸人中,“现代语言学之父” 索绪尔的贡献尤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完成了语言学从历时性研究到共时性研究的革命性转换,他否定那种关于主体的“实体”的观点,而赞成一种“关系”的观点,认为语言研究不仅应该根据语言的个别部分,不仅应该进行历时的研究,而且应该进行共时的研究,也就是将语言看作为一种完整的形式,一个统一的“领域”,一个自足的系统来研究。[11]语言系统内的各要素本身并无实际的意义,只有在系统内各要素的相互对比中才有意义,它们的关系是结构性的。为此,他提出并区分了一系列对立的概念: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共时和历时、横组合关系与纵聚合关系。索绪尔的这些思想、概念、术语将出现在《符号学原理》中。雅各布森是较早地关注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俄国语言学家,他进一步发展了索绪尔的横组合与纵聚合思想,将其称作“转喻”与“隐喻”,应用此来分析诗歌。上述诸人持续不断的努力,为20世纪语言学带来了革命,也为其他学科带来了革命,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就是语言学革命所带来的成果之一。
在巴特的著作中,随处可见语言学模式的痕迹。《神话》中指
出许多大众文化形式如广告、电影演员、脱衣舞表演等都是“神话”,巴特认为这些神话形式是“言谈”、是“讯息”,也就是相当于语言学概念中的“言语”,因此,对神话意义运作程序的分析要借助语言学中的含蓄意指概念。《符号学原理》是巴特旨在建构符号学大厦、系统地阐述符号学理论的著作。巴特在《导论》中说:“符号学知识实际上只可能是对语言学知识的一种模仿”,“我在此提出的这本《符号学原理》其目的只是要从语言学中引出一些分析概念……我们满足于提出和阐述一套术语系统,希望这套术语系统能够在大量异质性的意指现象中导出一个秩序来(即使它只是临时性的)。”[12]在书中,他依据结构主义语言学将符号学原理分为四类:I、语言和言语 II、能指和所指 III、系统和组合段 IV、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在前三类的分析中,巴特均先讨论该术语作为语言学概念的情况,后讨论其应用到符号学领域的情况,指出,由于社会符号的物质性,这三对概念应用到符号学领域时需加以改变。讨论时,巴特多以具体情况为例说明,显示出他实践的一面。如讲到组合段和系统时,对衣服、饮食、家具做了分析,其中对衣服的分析可看作另一本著作《流行体系》的萌芽。在“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部分,巴特分析了“含蓄意指”、“元语言”概念,这是一对由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提出的概念,巴特对它的分析依然是语言学的。由此,巴特初步建立了一门以语言学为理论内核,以非语言符号为研究对象的符号学科学,语言学分析的方法进入社会符号研究领域后,呈现出新的面貌,具有新的特性,可以称之为符号学方法,他的符号学方法在《流行体系》中得到了具体的应用。
可以见出,巴特符号学理论的概念、术语,甚至分析方法均来自语言学理论,他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自己符号学理论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依据,从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原则、模式出发,初步建立了一座以社会符号为研究对象的符号学理论大厦,这在符号学的发展中功不可没,《符号学原理》成为符号学入门的必读书。由于他的语言学依托,其符号学思想具有极强的科学性、可操作性,也正由于此,当他面对丰富复杂的社会符号时,侧重于建立一个类似于语言的系统,这个系统完全是封闭自足的。这就造成了他的两难处境:一方面想揭露社会的意义运作体系;另一方面其分析方法又将其局限在纯粹的共时性研究中,这样他的分析就不能充分基于社会语境和历史语境,显示出非历史化缺陷。
二、语言乌托邦:巴特符号学理论的理论实质
巴特的符号学大厦完全建立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地基之上,他的符号学理论在20世纪西方哲学、美学的语言论转向潮流中具有严格意义上的语言乌托邦性质。
所谓语言乌托邦,本文中有三层含义:(1)语言性,巴特自始至终都关注语言,语言学模式是他符号学理论的第一性原理。这在第一部分的论述中已可见一斑。(2)乌托邦性,即幻想性,巴特的符号学具有一种理想色彩或幻想的性质。这种乌托邦性的表现是,首先,他心目中的语言是“清新”的、“零度”的语言(仅指在符号学建构时期),这种语言是不存在的;其次,他认为符号学是一门元科学,即一切科学的科学,是其他科学的基础,它可以解决现实中一切问题,事实上,符号学也只是科学百花园中的一朵花,不可能仅凭自身来解决人类一切难题,这无疑也具有幻想性。(3)语言乌托邦性,如王一川所言:“意为语言性或语言论乌托邦,亦即符号性或符号论乌托邦。我们用它指20世纪西方美
学的语言理想范型崇拜倾向,这意味着关于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或现代传播媒介问题的探索,被认为是解决美学问题、探索审美和艺术奥妙的理想途径。”[13]
关于巴特符号学理论的这种语言乌托邦性质,笔者拟先从巴特《写作的零度》中的语言观谈起:[14]
在《写作的零度》中,巴特就已开始规划文学和审美的语言拯救之路。巴特认为,语言是具有伦理、历史性质的东西,它带有主体或本体意义,“语言结构仅只是一种人类的地平线,它从远处建立了某种熟悉性,而且其性质是否定性的”。[15]文学就是语言写作。在1848之年前,作家未意识到语言的控制力量,他们运用的是未经改造的资产阶级语言,因此,他们的写作是植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写作;1848年之后,作家意识到语言的强制性,开始有意识的创造一种自由的语言,尝试进行“白色”写作、“零度”写作,即植根于语言之外的写作,巴特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写作,而如果“写作永远植根于语言之外”,这种文学写作被他看作是“语言的乌托邦”:
文学的写作仍然是对语言至福境界的一种热切的想象,它紧忙地朝向一种梦想的语言,这种语言的清新性借助某种理想的预期作用,象征了一个新亚当世界的完美,在这个世界里语言不再是疏离错乱的了。写作的扩增将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学,如果这种文学仅是为了如下的目的才创新其语言的话,这就是:文学应成为语言的乌托邦。[16]
这里把文学写作看成是拯救语言、使其提升到“至福境界”的理想途径,即文学是语言的乌托邦。文学语言在此指的是一种
“中性”的、“零度”的语言,它去除了伦理、去除了历史,因此,可以说,文学是语言的乌托邦,语言也是文学的乌托邦。语言成为拯救文学和审美的惟一坦途,巴特的符号学就呈现出鲜明的乌托邦性质。巴特的这种语言观在后来得到了明确化:语言的本质是文学,两者是同质的。“结构主义本身是从语言范例中发展起来的,却在文学这个语言的作品中找到一个亲密无间的对象:两者是同质的。”[17]我们说,巴特的语言观无疑是一种乌托邦幻想,不可能存在着一种“中性”的、“零度”的语言,那么通过语言来拯救文学和审美也只能是不切实际的梦想,语言永远都是历史的,甚至它还与权力有某种关系。
巴特看到了语言的解放和拯救功能,《神话》中他用语言学中的含蓄意指概念对大众文化做了独出心裁的解释,揭示了社会符号的意义运作过程,指出了神话的意识形态性,显示了语言学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的切实可行性。也许正是鉴于对神话的成功分析,巴特才做起符号学的迷梦,以为可以依照语言学模式,建立一个包罗万象、可以揭示一切社会符号意义的符号学大厦。他确实依据语言学理论初步建立了一门符号学科学,并引导后来人在这方面努力,如意大利学者艾柯等。巴特自己在符号学的建构方面也做了不懈的努力,1964年,他出版纯符号学理论著作《符号学原理》,1967年,出版用符号学方法分析流行杂志上书写服装的专著《流行体系》,此时,巴特符号学理论的语言乌托邦性质已达到极致。
然而,符号学大厦还仅是初具规模,而且这座大厦存在着自身难以弥合的裂缝(这也说明了符号学的乌托邦性),因为语言不仅是乌托邦,它也是法西斯,不仅是肯定性的,也是否定性的。语言的肯定性是指语言表达意义的确定性、语言结构规范性、以
及语言模式的系统性、完整性、可操作性。语言的否定性是指语
言表达意义的不确定性、语言结构的强迫性、以及语言模式的不可靠性。语言的肯定性与语言的否定性二者同体共存,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巴特对语言的否定性的认识在《流行体系》的绪言中已显露出来。
《流行体系》中,巴特运用符号学方法详尽地分析了流行杂志上的书写服装,对符号学方法做了一次检验和实践,可以看出,符号学方法是有效的。绪言里,巴特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假设,即逆转索绪尔的主张(语言学是符号学的一部分):“或许,我们应该颠覆索绪尔的体系,宣布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因为不仅语言学是符号学中最为先进的一门科学,不仅语言学的方法为其他符号系统、亚符号系统以及亚语言系统提供了科学的、行之有效的一整套概念、方法、术语和逻辑,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所有的符号系统、亚符号系统或亚语言系统,无论其是否以语言作为表达交际或隐喻象征的工具或材料,在其实际运作过程中,无不遵循着语言学所描述的内在机制、规律与方法。尽管符号系统内部诸子系统、诸亚系统各具其自身的特点,然而我们都可以用语言学的方法去加以分类、归纳、描述与演绎。这种思想一方面使语言乌托邦达到了极致,另一方面,它其中还内含一层含义,那就是社会中一切诸符号系统都必须用语言来描述,语言是它们得以产生的母体。《流行体系》中,巴特将服装系统分为三个层次:真.
实服装
...(生活中真正的服装,作为物质存在的服装)、意象服装
....(杂
志上以摄影或绘图的形式呈现的服装)、书写服装
....(杂志上将意象服装描述出来的语言)。他谈论的是“写出来”的服装,是杂志上用来描写服装的语言。书写服装首先作为语言而存在,它一方面指向真实的服装,真实的服装体系是书写服装存在的地平线;另一方面,
它又自成一个系统,遵循自身的书写逻辑,这个逻辑即是杂志制造流行的逻辑。书写服装支配了真实服装的意义,人们对真实服装的取舍完全依赖杂志对流行的表述,因此,语言参与了意义的构成。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语言无所不在,它是法西斯。可见,巴特符号学在语言乌托邦的建构中已包含了解构的种子。
纵观巴特一生的思想,语言的肯定性力量和否定性力量相互交织,在符号学时期,他侧重于语言的肯定性力量,力图建立一个语言乌托邦王国,在那时,语言、语言学可以解决文学、审美、社会生活的一切问题,可以对它们提供一个明晰有效的解释,但语言的肯定性与否定性是内在于语言自身的,当巴特走向肯定性方面的极端时,也便必然的走向它的反面:语言的否定性方面,这便是后期的巴特。
三、神话和解神话:巴特符号学理论的社会学主
题
巴特将符号学与社会批评联系起来,致力于揭示社会符号现象的二级意义,指出在一切看似自然、合理的现象背后存在着惊人的意义制造过程。这就是神话。
(一)神话和解神话
“神话”一语,罗兰?巴特在《神话》中提出。《神话》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流行神话”,巴特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现象进行分析,如摔跤表演、脱衣舞表演、竞选等,后一部分是“现代神话”,是对前一部分的分析进行理论提升,系统化。巴特对神话
的分析是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的。
“现代神话”部分,巴特对神话做了规定:神话,首先是一种言谈,一种“传播体系”,“一种讯息”,“神话并非凭借其讯息的客体来定义,而是以它说出这个讯息的方式来定义的:神话的形式是有限制的,并没有所谓‘实质上’的神话”。[18]巴特认为“神话”这一社会现象类似于语言中的个别“言语”,它背后存在着一定的语言结构,因此,神话不是由其自身来定义,而是由神话背后的规则即“说出这个讯息的方式来定义”。如同语言中的言语,神话不是实质上的,而是结构性的。神话和内容无关,它由某种讯息、言谈的方式来决定,也就是神话化;神话是历史的。巴特从意义构成程序的角度来看待神话:“神话是一个奇特的系统,它从一个比它早存在的符号学链上被建构:它是一个第二秩序的符号学系统。那是在第一个系统中的一个符号(也就是一个概念和一个意象相连的整体),在第二个系统中变成一个能指。”[19]此意如列表说明:
语
神言
话
这是从理论上分析,从实例上看,巴特在《神话》中举了一
个颇负盛名的例子,即他对在理发店中看到的《巴黎——竞赛》
画报封面的分析:“封面上,是一个穿着法国军服的年轻黑人在敬
礼,双眼上扬,也许凝神注视着一面法国国旗。”就这一画面,用
上表分析,可以看到,从语言层面看,能指是画面,所指是画面的
含义:一个穿着法国军服的年轻黑人在敬礼,它们组成一个符号,这一符号作为能指进入下一个系统,和它的所指(在此是法国和军队有意的混合)结合,于是,一个神话诞生了:“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她的所有子民,没有肤色歧视,忠实地在她的旗帜下服务。”
巴特将第一系统称为语言——客体,第二系统称为元语言,可以看到,巴特此时对符号学的应用还不太熟练,犯了一个术语上的错误,元语言应为含蓄意指,这点巴特在《符号学原理》中做了修正。巴特通过含蓄意指概念将符号学与解神话计划结合起来。
巴特对神话的运作方式做了详尽的分析,为了分析的方便,他对术语做了改变,第一系统的最终名词,即语言层面上的符号,成为“意义”,意义在神话层面称为“形式”,神话层面上的所指称为“概念”,二者的关联为“意指作用”,通过这一改变,形象地说明了人们是如何将一个“讯息”变为“神话”的。于是,上表变为如下图示:
语
神言
话
可见,神话的能指既是意义又是形式,既充实又空洞,它一
方面有丰富的意义,另一方面又被耗尽,成为空洞的形式,是一
个载体。在从意义到形式的转变中,形式只是耗尽意义的资源,
使其可以被操纵,并随时可以从中取得营养,即利用意义,在意
义与形式不间断的躲迷藏游戏中神话因此而被定义。形式将意义
耗尽,它则被概念吸收,通过概念,一种完整的历史情景被植入形式中。概念具有丰富性和不确定性。形式与概念结合产生了第二系统,与第一系统一起形成了神话。由于能指的两面性,神话就显示出了两种功能:表意与告知,它使人理解并迫使人理解。这一分析揭示了神话活动中的虚构方式,人为的意义添加在一个自然的现象之上,这一添加是在人们毫不知觉的情况下完成的,当人阅读神话时并未意识到意义的添加,而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神话的目的,使人不知不觉中受其影响,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企图。
所谓“解神话”,在《神话》中,巴特将神话定义为“去政治化的言谈”,因此,“神话”是一个社会构造出来用以使自身存在合理化和合法化的种种隐秘的意象和信仰系统,所以巴特对神话的解神化针对的就是,布尔乔亚阶级如何以匿名的方式将其意识形态强加在所有社会阶层之上,也就是布尔乔亚阶级利用伪意识所进行的社会控制和普罗阶级的布尔乔亚化。[20]巴特的解神话计划具有极强的政治反抗性。推而广之,“解神话”就是指出神话的运作方式,以清醒的思考来破除迷思。巴特眼中的神话是以大众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它的“解神话”就与大众文化研究联系起来,也就把符号学与大众文化研究联系起来。“解神话”可以用于各种社会现象分析,包括神话、历史、社会事件等。我们生活在一个符号化的世界中,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神话,如当代中国关于足球教练米卢的神话,即一个人可以拯救一支球队,进而一个球队冲进世界杯可以证明一个民族强大的神话。
巴特对流行杂志上书写服装的分析可看作解神话的一个成功范例。此处,它解的是“流行神话”。在《流行体系》中,巴特对书写服装展开了精细的符号学分析,严密地说明了书写服装如何
制造了流行神话。从他对一个例子的分析中可见一斑。如“印花布衣服赢得了大赛”这句话,他将其分为四个层次:
4.修辞系统
3.流行的含
蓄意指
2.书写服饰
符码
1.真实服饰符码
在第一系统,即真实世界中,能指“印花布衣服”,所指“大赛”,“印花布衣服”是“大赛”的符号,明确的世事(印花布衣服赢得大赛这一确定的事实)用语言表达出来,就上升到术语系统(书写服饰符码):能指为表述所必需的语音实体即句子(“印花布衣服赢得了大赛”这一句子的语音实体),所指就是这句话所体现的概念即命题。可以肯定,印花布衣服和大赛、服装和世事之间具有同义[21]关系,它们的同义只是由于它标示(意指)着流行才产生(书写)的。换句话说,在大赛中穿上印花布衣服反过来变成了一个新的所指(流行)的能指。但是,因为这个所指只是鉴于世事与服装的同义才被书写出来,因此,同义本身这个概念就成了流行系统的能指,它的所指是流行。在整个系统被确立之后,我们面对着一个新的典型符号,其能指是完整形式的流行表述,其所指是杂志制造或者试图赋予世事和流行的表象。整个系统暗指:(1)印花布衣服是流行的;(2)印花布衣服与比赛的结合在某种社交场合是适当的;(3)印花布衣服是社交胜利的重要而积极的因素。[22]因此,书写服装制造了大量意义,杂志是一台制造流行的机器,杂志的习惯用语 世事的表象 标 写 流 行 句 子 命 题 衣服 世事
符号学理论中的“符号”
一、什么是符号 “符号”(sign)一词渊源已久,然而它的含义却一直含混不清,甚至在经典著作家那里也往往有不同的理解。 古代希腊,符号就是征兆。公元前5-4世纪,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把病人的“症候”看作符号,世称“符号学之父”。公元2世纪,古罗马医生、哲学家盖伦(Galen,C.)写了一本症候学的书,名为“Semiotics”,即今天人们所说的“符号学”。此后,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Augustine,A.)给了符号一个一般性的解释:“符号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使我们想到在这个东西加诸感觉印象之外的某种东西。”意思是说,符号是代表某一事物的另一事物,它既是物质对象,也是心理效果。奥古斯丁的符号观,直接影响了现代符号学的两位奠基人——索绪尔和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17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Locke,J.)把科学分为三种,第一二两种为物理学和伦理学,而第三种,他说“可以叫做Semiotic,就是所谓符号之学。各种符号因为大部分是文字,所以这种学问,也叫做逻辑学。”洛克的符号学说,更是皮尔斯符号学思想的泉源。 古代中国虽然没有关于“符号”的明确界说,但是古代汉字“符”确实含有“符号”的意思。所谓“符瑞”,就是指吉祥的征兆;“符节”和“符契”都是作为信物的符号;“符箓”为道教的神秘符号。先秦时期公孙龙《指物论》,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符号学专论。在古籍《尚书》中,注释者说:“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不仅说明了语言是一种符号,而且指出文字是记录语言符号的书写符号。 “符号”作为符号学的基本概念可以不加定义,但必须予以诠释。直到20世纪初年,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把语言符号解释为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体时,“符号”一词才算有了比较确定的含义,人们对于“符号”的理解逐渐趋于一致。 在索绪尔看来,符号不是别的,而是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关系。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索绪尔所说的“能指”(signifier),指的是语言符号的“音响形象”,所指(signified)是它所表达的概念。索绪尔把它们比作一张纸,思想(概念)是纸的正面,声音是纸的反面,它们永远处在不可分离的统一体中。他还认为,这是语言符号两个最为重要的特征。索绪尔说:“我们建议保留用‘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后两个术语的好处是既能表明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又能表明它们和它们所从属的整体间的对立。至于‘符号’,如果我们认为可以满意,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用什么去代替,日常用语没有提出任何别的术语。” 索绪尔关于符号的二元关系理论,很快地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因而也就澄清了数千年来对于“符号”一词的混乱解释。其实,符号是一种关系。索绪尔所说的“能指”,就是符号形式,亦即符号的形体;“所指”即是符号内容,也就是符号能指所传达的思想感情,或曰“意义”。符号就是能指和所指,亦即形式和内容所构成的二元关系。 应用索绪尔二元关系的符号理论,可以很方便地解释一切符号现象,分清楚什么是符号,什么不是符号。例如中国的“龙”是符号,那种奇特的动物形象是符号的能指,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是所指;恐龙时代的那些恐龙不是符号。交通路口的信号灯是符号,红灯或绿灯是能指,“禁止通行”或“允许通行”的含义是所指;家庭里用作照明的灯不是符号。“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也是一种符号,“月晕”和“础润”是能指,传达“风雨先兆”的讯息是所指。如此等等。 在索绪尔提出符号二元关系理论的同时,美国哲学家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提出了符号的三元关系理论。皮尔斯把符号解释为符号形体(representamen)、符号对象(object)和符号解释(interpretant)的三元关系。符号形体是“某种对某人来说在某一方面或以某种能力代表某一事物的东西”;符号对象就是符号形体所代表的那个“某一事物”;符号解释也称为解释项,即符号使用者对符号形体所传达的关于符号对象的讯息,亦即意义。在皮尔斯看来,正是这种三元关系决定了符号过程(semiosis)的本质。
皮尔斯Peirce
意指三分式tripartitesemiosis 皮尔斯把符号的可感知部分,称为“再现体”(representamen),相当于索绪尔 所说的能指;但是索绪尔的所指,在皮尔斯那里分成了两个部分:“符号所代替的,是对象(object)”,而“符号引发的思想”,称为符号的“解释项”。 对象object 符号直接所指的事物称为object,译为“对象”较为合适。对象,是皮尔斯理论中符号的第二个构成要素,另外两个是再现体和解释项。皮尔斯关于对象有一个非常宽泛的理解:“它可以是一个已知的独立存在的事物或者人们确定相信它存在过或认为它存在的事物,或者是这种事物的集合,或者是一种质、一种关系、一个事实,这种事物可能是一种集合,也可能是部分组成的整体,或者它有其他的存在模式,比如一种允许其存在不阻止它的消极性也被同样允许的行动,或者某种普遍的自然的欲望,或者总是基于某种普遍情况的事物”(Peircel936—1958:2.232)。 再现体representamen 皮尔斯的术语,指符号构成的第一个要素,另外两个是对象和解释项。在皮尔斯的论述中,再现体(representamen)常常等同于“符号(sign)”一词。皮尔斯最初对 再现体的定义是:“符号或再现体,对某个人来说,它在某个方面或以某种身份代表某个事物”(Peirce1936—1958:2.228);后来对再现体的定义则表述为:“符号,或者再现体,是一种第一性,它在真正的三元关系中表示被称为它的对象的第二性,并决定被称为它的解释项的第三性以同样的三元关系表示对象,而它自己也指称这个对象”(Peirce1936—1958:2.274)。 再现representation 皮尔斯最早论述符号本质时所使用的术语,一部份中国学者译此词为“表征”。再现是符号化的过程,即赋予感知以意义。皮尔斯将再现与能够真正理解符号的意识联系起来。汉语文献中关于这个概念的讨论,有时候与“表现”(expression)混淆。
罗兰巴特 作者之死
罗兰.巴特《作者之死》 在奥诺·巴尔扎克[1]的小说《萨拉辛》[2]中,描述了一位装扮成女人的被阉割的男歌手,写了这么一段话:“那是一位女人,她经常突然露出惊怕,经常毫无理智地表现出任性,经常本能地精神恍惚,经常毫无原因地大发脾气,她爱虚张声势,但感情上却细腻而迷人。”是谁在这样说呢?是乐于不想知道以女人身相出现的那位被阉割男人的小说主人公吗?是巴尔扎克本人因其个人经验而具有女人的哲学吗?是宣扬女性“文学”观念的作者巴尔扎克吗?是普遍都有的智慧吗?是具有浪漫色彩的心理吗?人们将永远不会知道,其实在的原因便是,写作是对任何声音、任何起因的破坏。写作,就是使我们的主体在中其销声匿迹的中性体、混合体和斜肌,就是使任何身份——从写作的躯体的身份开始——都会在中消失的黑白透视片。 情况大概总是这样:一件事一经叙述——不再是为了直接对现实发生作用,而是为了一些无对象的目的,也就是说,最终除了象征活动的练习本身,而不具任何功用——,那么,这种脱离就会产生,声音就会失去其起因,作者就会步入他自己的死亡,写作也就开始了。不过,对这一现象的感觉是多种多样的;在人种志社会里,叙事从来都不是由哪个人来承担的,而是由一位中介者——萨满或讲述人来承担,因此,必要时,人们可以欣赏“成就”(即对叙述规则的掌握能力),而从来都不能欣赏“天才”。作者是一位近现代人物,是由我们的社会所产生的,当时的情况是,我们的社会在与英格兰的经验主义、法国的理性主义和个人对改革的信仰一起脱离中世纪时,发现了个人的魅力,或者像有人更郑重地说的那样,发现了“人性的人”。因此,在文学方面,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概括与结果的实证主义赋予作者“本人”以最大的关注,是合乎逻辑的。作者至今在文学史教材中、在作家的传记中、在各种文学杂志的采访录中、以及在有意以写私人日记而把其个人与其作品连在一起的文学家们的意识本身之中,到处可见;人们在日常文化中所能找到的文学的意象,(都专横地集中在作者方面,即集中在他的个人、他的历史、他的爱好和他的激情方面;在多数情况下,文学批评在于说明,波德莱尔的作品是波德莱尔这个人的失败记录,凡高[3]的作品是他的疯狂的记录,柴可夫斯基[4]的作品是其堕落的记录:好作品的解释总是从生产作品的人一侧寻找,就好像透过虚构故事的或明或暗的讽喻最终总是唯一的同一个人即作者的声音在提供其“秘闻”。 尽管作者的王国仍十分强大(新批评仅仅通常是加强这种王国),不言而喻,某些作家长期以来已试图动摇这个王国。在法国,可以说,是马拉美首先充分地看到和预见到,有必要用言语活动本身取代直到当时一直被认为是言语活动主人的人;与我们的看法一样,他认为,是言语活动在说话,而不是作者;写作,是通过一种先决的非人格性——在任何时刻都不能与现实主义小说家的具有阉割能力的客观性混为一谈一一而达到这样一点,即只有言语活动在行动,在“出色地表现”,而没有“自我”:马拉美的全部诗学理论在于取消作者而崇尚写作(我们下面会看到,这一点使他的位置等于了读者)。瓦莱里[5]由于完全纠缠于一种有关自我的心理学,而大大地淡化了马拉美的理论,但是,他却从兴趣出发从古典主义转到了修辞学内容,他不曾停止过怀疑和嘲笑作者,他强调语言学本性,而且,作为他的“大胆的”活动,他在其全部散文书籍中要求文学考虑
符号学
符号学是研究事物符号的本质、符号的发展变化规律、符号的各种意义以及符号与人类多种活动之间的关系。符号学的原理应用到各具体领域就产生了部门符号学。[1] 中文名符号学外文名Semiotics定义关于意义活动的学说创始人索绪尔、皮尔斯 目录 1 符号定义 2 符号学定义 3 学科历史 4 中国符号学 5 学派之争 6 主要学派 ?瑞士索绪尔 ?俄国 ?原苏联 ?法国 ?美国 ?意大利 7 皮尔斯符号学 8 四个发展模式 9 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10 相关书目 符号定义编辑 西方著作给“符号学”的定义一般都是:“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学说”(Semiotics is the study of signs)。这个定义实际上来自索绪尔,索绪尔一百多年前建议建立一个叫做“符号学”的学科,它将是“研究符号作为社会生活一部分的作用的科学”。索绪尔并不是下定义,而是在给他从希腊词根生造的semiologie(来自希腊词seme?on)一词作解释,用一个拉丁词源词解释一个同义的希腊词源词,这在西方是有道理的。 然而索绪尔这句解释成了符号学的正式定义。在中文里这话是同词反复;在西文中,如果能说清什么是符号,勉强可以算一个定义。 但“什么是符号?”是一个更棘手的难题。很多符号学家认为,符号无法定义。赵毅衡给了符号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作为讨论的出发点: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反过来说: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表达,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这个定义,看起来简单而清楚,翻来覆去说的是符号与意义的锁合关系。实际上这定义卷入一连串至今难以明确解答的难题,甚至可以得出一系列令人吃惊的结论。 首先,既然任何意义活动必然是符号过程,既然意义不可能脱离符号,那么意义必然是符号的意义,符号就不仅是表达意义的工具或载体,
罗兰巴特1
浅谈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 摘要:作为20世纪著名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对当代法国文学界以及当今整个学术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是其他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难以企及的。他的文本理论颠覆了传统文艺批评中作者的权威地位,同时又与新批评“作品至上”的观点不同,提出了读者参与文本创作、使作品能指意义增殖的看法,并强调作者在写作时不应涉入主观情感和价值观念,即零度写作。 关键词:结构主义文本阅读读者零度写作 罗兰·巴特,法国当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家,是结构主义大师,同时又是后结构主义思想的倡导者和支持者。除了文学,他的思想理论渗透至哲学、符号学、语言学、社会学、时装、摄影、广告等各个领域,故著名批评家卡勒·乔内森称他为“多才多艺的人”。本文主要针对巴特的文本理论进行简要的论述,从解释文本内涵、分析巴特理论中阅读以及读者的重要性、巴特的零度写作这几个角度进行概述。 巴特的文本理论是在对作品与文本进行区分的基础上,对文本的特点、分类以及如何创造文本的一系列关照。他认为,文本的意义并不来自外部实在,而是来自内部的差异系统的永不确定的流变。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中,批评家致力于寻找语言之外的那个永恒不变的终极所值。但巴特的文本理论则指出,文本具有复数性和互文性,故将文本分为可写性文本与可读性文本。并指出,作家在创作时不应涉入主观情感,提倡零度写作。 一、一个结构主义者的转变 (一)从德里达到罗兰·巴特 巴特在1972年给让·里斯塔的一封信中承认了德里达对自己的影响:“帮助我,让我明白了我面临的(哲学的,意识形态的)关键问题是什么。他使结构失去了平衡,使符号变为开放的。”① 德里达认为,言语中心主义及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西方形而上学之源。言语
皮尔斯符号理论对当代的影响
皮尔斯符号理论对当代的影响作者:颜青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符号学广义上是研究符号传意的人文学科,涵盖了所有涉及文字符、讯号符、密码、古文明记号、手语的科学,当今所指的符号学是随着20世纪下半期结构主义的兴起而出现的,其源头主要有三个:胡塞尔(E.EdmundHusserl,1859-1938)的现象学、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1857-1913)的结构主义和皮尔斯(CharlesSandersPeirce,1839-1914)的实用主义。与索绪尔将符号分为互不从属的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不同,皮尔斯认为符号由不可分割的对象(Object)、表象(SignorRepresenta-men)和解释项(Interpretant)三部分构成。皮尔斯符号学是认知的符号学,他认为逻辑学和符号学是哲学的同一个分支,对符号过程的非事实形式不感兴趣,尽管后来他也懊悔没有公正地对待美学。由此,人们对皮尔斯符号学通常从认识论视角研究,挖掘其认知价值,但却忽略了其与美学相关的问题。虽然皮尔斯从未在其著作中明确表述符号过程的美学维度,但只要仔细分析,仍可发现其符号过程的不明推论(Abduction)[1]步骤自身就具有美学维度,而这一维度是艺术表达的基础。本文从皮尔斯实用主义与符号学的关联开始,着重分析美学维度是如何在符号过程的不明推论中显现的,指出其所包含的本质要素是符号的冲突,围绕这一观点展开与此相关的美学讨论,深化对皮尔斯符号学的认识,展现其价值深度,拓展研究视域。 一、皮尔斯实用主义与其符号学的关联
皮尔斯是美国实用主义的创始人,正如他认为自己首先是符号学家,他的实用主义与符号学联系紧密。皮尔斯的实用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意义理论,为了弄清词或概念的意义,他提出了实用主义原则,认为效果和可能有的实际关系是我们的概念对象所具有的,我们对这些效果的概念就是我们对对象概念的全部。在他看来,实用主义本身并不是关于形而上学的学说,不试图确定任何事物的真理性,它只是一种发现现实的词和抽象概念的意义的方法。也就是说,实用主义是一种科学的逻辑或科学方法论,用它来分析各种符号(包括词、观念、思想)的意义,以确定信念、采取行动并达到目的。关于理智概念的“意义”是什么,皮尔斯认为只能通过研究符号的解释项或符号固有的意味效果加以解决。他将符号的解释项分为情感解释项(e-motionalinterpretant)、精力解释项(energeticin-terpretant)和逻辑解释项(logicinterpretant)。一个符号所固有的头一种解释项就是符号所产生的情感,我们几乎总会把某种感情解释为表明我们已经理解这个符号的固有效果的证明,而这种情感就是“情感解释项”,在某些情况下,它是符号产生的唯一固有效果。比如,一首乐曲的演奏就是一个符号,它传达或者企图传达作曲家的音乐观念,不过这些观念通常不过是一连串的情感。以情感解释项为中介,一个符号可能会产生进一步的效果,在这种进一步的效果中往往包含着一种努力,这种努力就是“精力解释项”,它可能是一种肌肉的用力,但更通常是心理的努力,是对内心世界施加的努力。它是一种单一的活动,不具有普遍性,因此它不可能成为理智概念的意义。此外,符号还具有一类意味效果,它肯定与那些
恋人絮语 罗兰巴特
《恋人絮语》 罗兰巴特 *译者言—— 罗兰巴特和他的《恋人絮语》(汪耀进 文) 严谨的学术权威们像诸神一般在法国学坛的所谓“巴塞侬”神庙各就各位,虎踞龙盘,巴特却甘愿在神庙外的台阶廊沿(他所津津乐道的“边缘”)起舞弄清影,拣尽寒枝不肯栖。 已经很少有人再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巴特是继萨特之后的法国学界的另一位“现代大师”。……在许多人看来,巴特首先是结构主义思想家,是以结构主义眼光来打量文化现象的先驱;是他将符号学推向了法国学术界的前沿;是他勾勒了结构主义“文学科学”的蓝图。在另外一些人眼中,巴特又绝非是科学精神的体现者,而是一个追求快感乐趣的人本主义的化身。为满足快感而阅读,管他天王老子,无视清规戒律,我爱怎样读就怎样读。 巴特又被奉为学术界的“先锋派”。当法国新小说派代表罗伯格里耶等人的实验性小说被法国批评界斥为“不可卒读”时,巴特挺身而出,拔笔相助,并且断言:只有“不可卒读”才体现了文学的最终目的,因为它向读者的期待心理进行了挑战。由此,他力贬“可读性”作品,推崇“可写性”文本——读者不知怎样读,只能靠想象(边读边创作即“写作”)。 巴特借鉴了尼采的戏剧化守法,挣脱了超然局外的“元语言”的刻板束缚。转叙论述成了直接演示,行文成了“动真格的”话语。 《絮语》的结构匠心旨在反恋爱故事的结构。……巴特认为,对情话的感悟和灼见从根本上说是片段的、不连贯的。……巴特神往的就是“恋人心中掀起的语言波澜的湍流”(就像诗人叶芝从飞旋的舞姿中瞥见一种永恒的和谐一样)。“像一个细心的厨师,他留意不让语言变稠,变粘”(莱奇《解构主义引论》第112页) 在巴特看来,一个精心建构的首尾相顾、好事多磨的爱情故事是“社会以一种异己的语言让恋人与社会妥协的方式”(《Le grain de la voix》,第267页)。敷设这样一段故事不啻是编织一个束缚自己的罗网。真正为爱情而痛苦的恋人既没有从这种妥协中获益,也没有能成为这种爱情故事的主人公。爱情不可能构成故事,它只能是一番感受,几段思绪,诸般情境,寄托在一片痴愚之中,剪不断,理还乱。 书中的所谓“恋人”是一个符合体:纯洁幻想的恋人与智慧深邃的作者的结合,想象的激情与冷静的自制(表现力)的统一(就像任何一部作品的诞生一样)。这里,应该提醒读者体味巴特的“苦心”:反恋爱故事,即着力表现恋人的想象激情,而不是“故事”或“正确表达”。这种辞典式的罗列形式透出了一种冷静,是一种不加掩饰、文饰的表达方式。……恋人在这种虚拟的“存在”上宣泄恋物、象征和释义的激情。这一模式在西方自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14世纪诗人彼得拉克始,就不知有多少文人骚客竞相搬弄演衍。巴特的独创之处是赋予其浓厚的符号学色彩。热恋中的自我是一部热情的机器,拼命制造符号,然后供自己消费。 说到底,《絮语》便是对正在叙述中的恋人的写照……展示了一个充分体现主体意义的“我”,呈现为一种产生、发展、建构、流动、开放的过程。……是语言铸就了主题,铸就了“我”。因此,《絮语》中的“我”是多元的、不确定的、无性别的、流动的、多声部的。 《絮语》又是一个典型的解构主义文本。……在巴特看来,任何文本都只不过是一个铺天盖地巨大意义网络上的一个扭结;它与四周的牵连千丝万缕,无一定向。这便是“文互涉关系”。 *正文
皮尔斯符号学视角下网络语言中象似符号的分析
Contents Contents 摘要 ............................................................................................................................... I Abstract ......................................................................................................................... III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1) 1.1 Research Background (1) 1.2 The Significance and the Methods of the Research (2) 1.3 Layout of the Thesis (3) Chapter Two Literature Review (5) 2.1 Research of Netspeak Abroad and at Home (5) 2.1.1 Research of Netspeak Abroad (5) 2.1.2 Research of Netspeak at Home (6) 2.2 Summary (9) Chapter Three Peirce’s Semiotics on Iconic Signs (10) 3.1 Semiotic Signs (10) 3.1.1 The Definition of Iconic Signs (10) 3.1.2 The Properties of Iconic Signs (13) 3.2 Summary (17) Chapter Four An Analysis of Iconic Signs of Netspeak (19) 4.1 General Survey on Netspeak (19) 4.1.1 The Definition of Netspeak (19) 4.1.2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tspeak (21) 4.1.3 Classification of Netspeak (24) 4.2 The Accounts of Iconic Signs in Netspeak (32) 4.2.1 Iconicity of Easily Memorable Words in Sound (33) 4.2.2 Iconicity of Neat Sentences in Form (42) 4.2.3 Iconicity of Various Mood Arrangements in Text (49) 4.3 Summary (54) Chapter Five Conclusion (55)
符号学理论
1,什么是符号学? 符号学,是一门研究符号,特别是研究关于语言符号的一般理论的科学,是十九世纪末才兴起的,符号学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目前主要研究符号的本质、符号的发展规律,符号与人类各种活动的关系,符号与人类思维的联系。(符号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符号学理论,在许多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且在认识论、社会生物学、宗教学、神话、文学、音乐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果。现在,世界各国和符号学家正在用符号学的观点来研究动物语言、宗教语言、法律语言、政治语言、广告语言等。) 一些学者对符号学的理解 “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管它叫符号学(semiologie)。它将告诉我们符号是由什么构成的,受什么规律支配。”(索绪尔,1980) 要研究是什么使得文字、图像或声音能变成讯息,就必须研究符号学,而研究符号和符号的运作的学问就是符号学(Fiske,1990,张锦华等译,1995:60)。 符号学(Semiotics)就是研究符号、指示会意和指示会意系统的一门科学。 符号学即关于记号(sign)、记号过程(semiosis)或记号系统的理论研究。(李幼蒸,1999: 45) 2,符号学的历史 符号学(semiotics,semiologie,semiotic)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法国和意大利为中心重新兴盛至欧洲各国,它的源头不外乎胡塞尔的现象学,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和皮尔斯的实用主义。 大约从本世纪60年代开始,符号学才作为一门学问得以研究。现在符号学已经成为一项科学研究,其理论成果也已经渗透到其他诸多学科之中。 符号的起源是劳动。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就有了实用和审美两种需求,并且已经开始从事原始的设计活动,以自觉或不自觉的符号行为丰富着生活。从我们祖先的结绳记事到歌舞图腾,都是维护社会传统秩序的信息符号。
历史的话语 罗兰-巴特
历史的话语 罗兰-巴特 人们对于比语句更大的语言单位(即话语,discourse)进行形式的描述,不是新的事情。从高尔吉亚[2]到十九世纪,它一直都是古典修辞学主要关心的问题。然而语言科学晚近的发展使人们对这一主题重新发生了兴趣,并且它还带来了处理这一问题的新颖技巧。现在,一门关于话语的语言学可以说已经跨入了可能性的门槛。它对文学分析——以及对于文学分析在其中起着很大作用的教育过程——所可能具有的意义使它成为符号学[3](semiology)当前重要的研究项目之一。 这样一种第二级的语言学的目标应该不只是去探求话语的一般性概念(如果存在的话),以及表达一般性概念的单位和结合规则,而且也应用于判定结构分析是否认可了传统的话语形态(discourse-genres)的类型学——譬如说,在把诗的和小说的话语、把虚构的和历史的叙述加以对比时,我们是否总是有道理的呢?这两组对比中的第二组也就是下面要探索的主题:实际上在事实的和想像的叙述之间有无任何特定的区别,有无任何语言学上的特征,按照这一特征,我们可以把适合于叙述历史事件的方式——一个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从属于历史“科学”规范的问题,它要求符合“实际发生的事情”这样的准则,并根据“合理的”说明原则来加以判断——与适合于史诗、小说或戏剧的方式加以区别吗?如果存在着这些区别特征,那么它们又影响着话语的哪些部分,以及在语言行为(languagye-act)的哪一点上起着作用呢?本文将通过对某些古典历史学名家如希罗多德、马基雅弗利、鲍绪埃[4]和米歇莱[5]的著作中的话语所做的非严谨的(并且绝非彻底的)考察,来对这个问题作一尝试性的解答。 一 首先,古典历史学家是在什么情况下在自己所写的话语中被引导(或被允许)去谈及表达话语的行为的呢?在话语中,像雅克布逊(不过他所关心的是分析语言,而不是分析话语)所说的那种标志着转入和转出自身指示(sui-referential)方式的转换语[6](shifters),采取的形式是什么呢? 历史话语似乎有两种标准类型的转换语。第一种可以称作审核方式(monitorial mode),它对应着雅克布逊所说的(还是在语言的层次上)证据类(evidential category);它把信息(报道的事件),代码陈述(报道者的作用部分)以及有关代码陈述的信息(作者对其资料来源的评价),组合在一起。因此,证据类显然包括了对于资料来源和见证者报道的各种论述,以及对引证其它原文的该史学家的报道行为的各种论述。这一方式的选择是不受限制的——史学家可能心安理得地默默使用着他的资料来源;但是一旦他选择了这一方式,他就接近于人种史学家的地位了,后者通常都需提供关于消息报道者的细节资料;因
罗兰·巴特
罗兰〃巴特 著作 主要有《写作的零度》(1953)、《神话》(1957)、《符号学基础》(1965)、《批评与真理》(1966)、《S/Z》(1970)、《文本的快乐》(1973)等等,影响了人们对文学和文化的看法,也可视为巴特对文学研究工程延伸而成的一套思想体系。 他提出写作的零度概念以反对萨特关于文学干预时事的理论,认为文学如同所有交流形式一样本质上是一个符号系统,并在多部著作中运用其文本分析法消解言语所指,尝试按照作品本身的组织原则和内部结构揭示文本种种因素的深层含义和背景。他概括出文本的三个层次,功能层、行为层(人物层)、叙述层,以此分析读者对文本的横向阅读和纵向阅读。受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影响很深。 巴特最早期的作品主要是对40年代存在主义思潮的回应,尤其是针对其代表人物萨特。在萨特的作品《什么是文学》中,他将自己从既已建立的书写形式以及他认为敌视读者的前卫书写形式中抽离。而巴特的回应是:何不寻找书写中那些特别而独创的元素。在《写作的零度》中巴特认为语言与形式都是呈现概念上的常规,而不完全是创意的表现。形式,或者是巴特所称的“书写”是个体选择以独特的方式操作形式上的常规来达到他所想达到的效果,这是一个独特且创造性的行动。当一个人书写的形式向大众发表以后,将无可避免的成为常规,这表示创作成为一种在持续不断改变与反应中的连续性历程。 于1967年发表了他最著名的论文“作者之死”,主要是受到雅克·德里达逐渐崛起的解构主义所影响,这篇论文变成为他向结构主义思想告别的转折。 1970年发表著名的作品《S/Z》,是对巴尔扎克小说作品《萨拉辛》的批判式阅读,被认为是巴特最为质量兼具的作品。整个70年代巴特持续的发展他的文学批评理论,发展出文本性与小说中的角色中立性等概念。 Readerly and writerly texts 可读性文本与可写性文本 罗兰〃巴尔特《S/Z》(1970)中的术语,原文为lisible和scriptable。《S/Z》是对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萨拉西尼》的评注,巴尔特用“可读性文本”和“可写性文本”区分传统小说与20世纪的文学作品,认为前者的意义是封闭的,后者则强迫读者去添加意义。如他所说:“可写性的文本是我们自己的写作,是在世界的无限运动……被某种减损多样性的单一系统(意识形态、类概念、批评)贯通、交叉、阻断或塑造之前,是意义框架的开放,是语言的无限。”可读性文本则只是“作品”(products)、而不是“创作”(productions)。类似的区分还可以见于艾柯的《作者的角色》(1981),相应的术语是“敞开的文本和封闭的文本”(open and closed texts)。 《恋人絮语》是一本无法让人定义的书。就像书名所显示的那样,它没有理论话语的漫漫征途却不乏深刻洞见。它没有小说文本的故事情节却不乏一个个让人回味流连的爱情场景。他貌似体贴的将恋人的心态和言语的方式安排成了这本书的结构方式,然而其后却不乏嘲弄。他用一种开放式,流动的,无定向性的言语方式开始了他对爱情的胡言乱语。 巴特精巧的勾勒恋爱状态的每一个场景,然而却并把他们有序的编排。所谓相遇,一见钟情,交谈倾诉,挫折误解,等待,依恋等等,诸种状态本身就毫无先后顺序可言,它们有时交替进行,有时同时发生。剪不断,理还乱的恋人心绪哪里有什么逻辑可言?因此巴特只能针对每一个场景进行勾勒分析。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巴特的分析是建立在恋人这一方,而以恋人爱上的对象为情偶之上的主体性分析。他用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维特所显示的心态做例,细致入微的分析每一种状态下的矛盾和潜台词。 昆德拉《好笑的爱》。
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探析
硕士电子版论文 保密级别内部学位级别文学硕士 论文提交日期:2002年5月 论文答辩日期:2002年6月 论文中文题名: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探析 论文英文题名:The Exploration of Roland Barthes’s Semiotics Theory 作者及所在单位:张青岭吉林大学文学院 指导教师及所在单位:张德厚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 分类标识:B83—064 中文主题标识:罗兰?巴特 符号学 神话 英文主题标识:Roland Barthes Semiotics Myth 中文文摘: 论文摘要 罗兰?巴特,20世纪法国重要的思想家、文艺批评家,其符号学理论具有极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然国内学者对此却鲜有论述,本文尝试之: 一、结构主义语言学:巴特符号学理论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依据 结构主义语言学指的是以索绪尔、雅各布森、叶尔姆斯列夫、乔姆斯基等人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理论。索绪尔的结构思想以及一系列概念术语为现代语言学奠定了基础,上述诸人不断努力,
完成了语言学上的革命。 巴特符号学理论中处处可见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一系列概念、术语、完全来自语言学,理论体系也是依照语言学的理论体系而建立,而且巴特用来分析社会中诸现象的符号学方法也来自语言学。 由是观之,巴特的符号学理论完全建基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之上,继承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优缺点:形式性、科学性、可操作性和非历史性。 二、语言乌托邦:巴特符号学理论的理论实质 巴特的符号学理论在20世纪西方哲学、美学的语言论转向中具有严格意义上的语言乌托邦性质。语言乌托邦,本文中,有三层含义:(1)语言性,语言模式是巴特符号学理论的第一性原理,他甚至颠覆索绪尔的假设,以符号学为语言学的分支;(2)乌托邦性,即幻想性,从零度写作到符号学大厦、元语言,均具有浓郁的理想化色彩;(3)语言乌托邦性,“意为语言性或语言论乌托邦,亦即符号性或符号论乌托邦。我们用它指20世纪西方美学的语言理想范型崇拜倾向,这意味着关于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或现代传播媒介问题的探索,被认为是解决美学问题、探索审美和艺术奥妙的理想途径。” 巴特认为语言和文学是同质的,二者互为乌托邦。 然而,巴特符号学理论的建构中也包含着解构的力量,庞大的符号学大厦中隐藏着裂缝,因为语言不仅是乌托邦,也是法西斯。当巴特对语言的崇拜达到极端时,必然走向它的反面,反语言,反乌托邦。 三、神话和解神话:巴特符号学理论的社会学主题 “神话”一语,出自巴特的《神话》,巴特从语言学的角度对
索绪尔和皮尔斯创建符号学的比较
两位符号学创始人的比较 岩山老林43h1010@https://www.360docs.net/doc/7510635238.html, 索绪尔和皮尔斯都是符号学界公认的两位创始人。将他们两位创始人的一些事作比较,不仅是一件有趣的事,而且可能引发一些有益的启迪。本文仅就已掌握的资料作粗略比较,不妥之处,但求指正。并以“抛砖引玉”之初衷,引发更多的思考。 1. 两位创始人是同时代的人。索绪尔(1857~1913),皮尔斯(1839—1914)。皮尔斯比索绪尔大18岁,两人辞世时间仅差一年。 2. 两位创始人的创建符号学理论的时期大体相同。索绪尔在1913年日内瓦大学讲课时提出了符号学。按在世时间分析,皮尔斯提出符号学理论的时间不会迟于1914年,或许比1913年更早。 3. 两位创始人符号学理论传世时间相差不大。索绪尔符号学理论的讲课笔记于1916年在瑞士洛桑出版。包含有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的皮尔斯八集论文集于20世纪30年代出版。按著作出版时间计算,索绪尔符号学理论“入世”早十余年。资料显示,索绪尔符号学理论到20世纪30年代已引起学界注意。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引起学界注意的具体时间缺乏资料考证,仅有资料显示大约在20世纪80~90年代。二者大约相距半个世纪。 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更先风行世界的原因是什么?或许是著作出版时间差引起,或许是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源于语言学,关注语言学的人群更多,语言学更容易接受。而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与逻辑学关联紧密,关注逻辑学的人群较少,逻辑学较难接受。 4. 两位创始人符号学理论的文本均非本人在世编著。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课程讲了三遍,三次课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但始终没有讲稿,似乎并没有兴趣写成一部著作。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是两个学生按收集的听课笔记整理出版的。皮尔斯一生也未出版过符号学方面的专著,也从未系统地归纳或精心地解释过他有关符号学的思想。他的《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论文集》(八卷)是后人整理出版的。研究皮尔斯的学者认为,皮尔斯的论文集缺乏系统性,甚至有些杂乱无
符号学
符号学 所属分类:史学理论学科名科学语言学 名称:符号学 符号学 英文名:(Semiotics 或Semiology) 符号学(semiotics)一词源自希腊语,seme(记号), 如semiotikos,意为对记号(sign)的解释。符号学即为对记号的解释或研究记号体系的功能。 目录[隐藏] ? 1 定义 ? 2 起源 ? 3 经典解读 ? 4 学派列表 ? 5 标识与符号学 ? 6 中国符号学研究 ?7 中国哲学和符号学 ?8 参考资料
符号学-定义 符号学(Semiotics 或Semiology)广义上是研究符号传意的人文科学,当中含盖所有涉文字符、讯号符、密码、古文明记号、手语的科学。可是,由于含盖的范围过于广阔,在西方世界的人文科学中并未得到重视,直至结构主义在二十世纪下半期兴起,以《Tel Quel》杂志为号召的哲学家,为了反对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主义,则大量引用俄罗斯在共产革命前的一系列,有关符号在文化上的再现过程的研究,故此,正式出现当今所指的符号学,要算到一九六零年代。 现代符号学另一个强大的源头是世纪初瑞士语言学泰斗索绪尔的教学讲稿﹣﹣《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将符号分成意符Signifier 和意指Signified 两个互不从属的部分之后,真正确立了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影响了后来李维史陀和罗兰·巴特等法国结构主义的学者,被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 符号学-起源 “符号学”的思想是在20世纪初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F.)首先提出的。“符号学”在英语中有两个意义相同的术语:semiology和semiotics,这两个词都用来指这门科学,它们的唯一区别在于,前者由索绪尔创造,欧洲人出于对他的尊敬,喜欢用这个术语;操英语的人喜欢使用后者,则出于他们对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Peirce,C.)的尊敬。 从20世纪符号学的发展状况来看,符号学研究的方向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语言学的、非语言学的和折衷的。索绪尔、叶姆斯列夫(Hjelmslev,L.)、巴特(Barthes,R.)为第一类,即带有语言学倾向的符号学研究方向;皮尔斯、莫里斯(Morris,C.)、西比奥克(Sebeok,T.)为第二类,即通常所说的一般符号学方向;艾柯(Eco,U.)和其他一些符号学家则为第三类。
何为符号 符号学理论
何为符号 以前符号是指代事物的工具,例如“红灯”表示“停止”,“绿灯”则表示“前进”,如图1所示,传统符号可以概括为“符号X指代Y”这种固定格式。美国逻辑学家、哲学家皮尔士(1)根据与Y,即指代对象之间的关系,把符号X分为以下三种表意形式范畴。 X Y 图1 传统符号观 类象符号(图形符号)是指在某一点上与指代对象相似。例如,语言上的拟声词、拟态词及隐喻等。引得符号是指直接或物理性地指示对象的一种表意形式,指代对象因因果关系、邻接性而产生。如温度计、敲门声等。最后一种形式——常规符号,它与指代对象习惯性地连接在一起。如苹果、狗、狼等概念性象征。 皮尔士的这种符号观并没有超越传统图式,即符号就是某种事物的替代,在震撼现代思想与现代文学理论的符号理论中,不得不提另一位符号学家的创新性符号理论,他的理论经常与皮尔士的理论相比较。那么,这种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符号理论的现代符号论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震撼现代的符号理论是由费尔迪南·德·索绪尔(2)创始的。索绪尔所指的符号已不再是指称事物的工具。那么,不作为工具的符号又是什么呢? 索绪尔对长期以来哲学家们所一直坚信不疑的信念提出了质疑。因为传统哲学家们认为“传统符号=语言”这一等式成立。也就是说,所谓语言就是指代其概念及指代对象的工具。对哲学家们来说,首先,世界上存在普遍概念及对象,而且用来指代这些事物的工具即语言也同样存在。因此,对哲学家们而言的语言的作用就是为了切实指代概念及对象物,而尽可能成为一种透明的工具。首先有概念及对象物的存在,然后以与其相对应的形式造出作为符号用的语言。这种传统语言观称为语言名称目录观。如果转为图表形式,则如图2所示。索绪尔否定了语言名称目录观,并展开了彻底反对的讨论。 图2 语言名称目录观 在我们生活着的世界上,在还未了解语言之前,我们不可能区分概念及事物,也不可能进行分类。也就是说,并不是概念及事物先于存在,而后才产生与之相对应的语言的。与此相反,而是语言出现之后才产生概念及事物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语言通过分割遥无边界的连续的现实世界,才出现了概念的轮廓和事物的形态。如果将索绪尔的主张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就是“先有语言”。如果用图表表示的话即如图3所示。
符号学理论中的“符号”
一、什么就是符号 “符号”(sign)一词渊源已久,然而它得含义却一直含混不清,甚至在经典著作家那里也往往有不同得理解。 古代希腊,符号就就是征兆。公元前5-4世纪,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把病人得“症候"瞧作符号,世称“符号学之父”。公元2世纪,古罗马医生、哲学家盖伦(Gale n,C、)写了一本症候学得书,名为“Semiotics”,即今天人们所说得“符号学”。此后,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Augustine,A、)给了符号一个一般性得解释:“符号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使我们想到在这个东西加诸感觉印象之外得某种东西。”意思就是说,符号就是代表某一事物得另一事物,它既就是物质对象,也就是心理效果。奥古斯丁得符号观,直接影响了现代符号学得两位奠基人-—索绪尔与皮尔斯得符号学思想。17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Lo cke,J、)把科学分为三种,第一二两种为物理学与伦理学,而第三种,她说“可以叫做Semiotic,就就是所谓符号之学。各种符号因为大部分就是文字,所以这种学问,也叫做逻辑学.”洛克得符号学说,更就是皮尔斯符号学思想得泉源。 古代中国虽然没有关于“符号”得明确界说,但就是古代汉字“符”确实含有“符号”得意思.所谓“符瑞”,就就是指吉祥得征兆;“符节"与“符契”都就是作为信物得符号;“符箓"为道教得神秘符号。先秦时期公孙龙《指物论》,可以说就是中国最早得符号学专论。在古籍《尚书》中,注释者说:“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不仅说明了语言就是一种符号,而且指出文字就是记录语言符号得书写符号。 “符号”作为符号学得基本概念可以不加定义,但必须予以诠释。直到20世纪初年,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把语言符号解释为能指与所指得结合体时,“符号”一词才算有了比较确定得含义,人们对于“符号”得理解逐渐趋于一致。 在索绪尔瞧来,符号不就是别得,而就是能指与所指得二元关系。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索绪尔所说得“能指”(signifier),指得就是语言符号得“音响形象”,所指(signified)就是它所表达得概念。索绪尔把它们比作一张纸,思想(概念)就是纸得正面,声音就是纸得反面,它们永远处在不可分离得统一体中。她还认为,这就是语言符号两个最为重要得特征。索绪尔说:“我们建议保留用‘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用所指与能指分别代替‘概念’与‘音响形象’。后两个术语得好处就是既能表明它们彼此间得对立,又能表明它们与它们所从属得整体间得对立.至于‘符号’,如果我们认为可以满意,那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用什么去代替,日常用语没有提出任何别得术语。" 索绪尔关于符号得二元关系理论,很快地得到学术界得公认,因而也就澄清了数千年来对于“符号”一词得混乱解释.其实,符号就是一种关系。索绪尔所说得“能指”,就就是符号形式,亦即符号得形体;“所指”即就是符号内容,也就就是符号能指所传达得思想感情,或曰“意义”.符号就就是能指与所指,亦即形式与内容所构成得二元关系. 应用索绪尔二元关系得符号理论,可以很方便地解释一切符号现象,分清楚什么就是符号,什么不就是符号。例如中国得“龙”就是符号,那种奇特得动物形象就是符号得能指,作为中华民族得象征就是所指;恐龙时代得那些恐龙不就是符号。交通路口得信号灯就是符号,红灯或绿灯就是能指,“禁止通行”或“允许通行”得含义就是所指;家庭里用作照明得灯不就是符号.“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也就是一种符号,“月晕”与“础润"就是能指,传达“风雨先兆”得讯息就是所指。如此等等. 在索绪尔提出符号二元关系理论得同时,美国哲学家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提出了符号得三元关系理论。皮尔斯把符号解释为符号形体(representamen)、符号对象(object)与符号解释(interpretant)得三元关系。符号形体就是“某种对某人来说在某一方面或以某种能力代表某一事物得东西”;符号对象就就是符号形体所代表得那个“某一事物”;符号解释也称为解释项,即符号使用者对符号形体所传达得关于符号对象得讯息,亦即意义.
